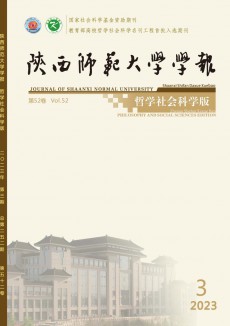唐代文學史的總體特征大全11篇
時間:2024-02-05 15:17:5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唐代文學史的總體特征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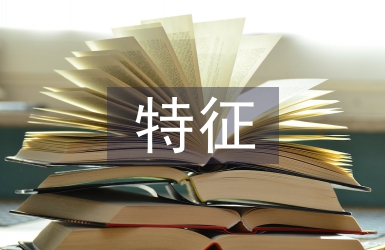
篇(1)
“史”是什么?中國文學史界(包括古代和現代)幾年來談得最多的是“重寫文學史”的課題,因為文學史著已有許多部,才談得上“重寫”。美學史的狀況卻不是這樣,它所解決的是原初性的建設,“重寫”還談不上。因上,新世紀的初始時期,美學史的撰寫只能處于起步階段。它雖然才起步,但起點較高,它應避免中國文學史撰寫中存在的缺陷,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免得日后再來“重寫”。
“史”寫什么?筆者概括為16個字:歷史復活,現時視界,現象描述,經驗揭示。前賢曾言,學術研究的對象是地下和地上的。這確定了研究的全部范圍。然而,地下的文物、地上的文獻,物化的或紙上的,都是死的,這就需要加以復活,即把“史”的過去時態所沉積下來的存在現象和事實復活起來,通俗地說,就是把死人復成活人,把美學理論家、把創造了美的實踐者真正當作生機飽滿、生氣盎然的活人,始終進行活的描述,使美學史成為活史。所謂現時視界,就是以現時代的當下美學史家的主體心態、觀念、視角、方法,對待彼時的美學史存在現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已成為一個普遍認同的命題,其內涵就在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人寫的,有著當代人的體認方式。美學史也是這樣,并從而構合為美學史的當下特征。所謂現象描述,因美是感性體的現象存在,所以現象描述有助于審美的歷史現象的復原,有助于生香活意的審美歷史現象的保鮮。美學史不僅要讓人們看到歷史上的人解說了什么,而且要讓人們看到他們創造了什么。所謂經驗揭示,是對美學史的發展歷程、經驗原因、軌跡線索的理性體認。這是美學史之深度所在。一些史著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史識。識,就是史家們主體識見的高度和深度凝結。史著變成了歷史上所曾經發生過的現象的堆積,毫無識見,這是成批量史著質量低下之原因所在。識見不管正確與否,但必須有深意,即使是偏見,也是深刻的偏見。美學史研究需要有智慧和深沉的思慮。
“史”應有史象——史的現象,還應有史感——體現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歷史感。現在的史著包括美學史著最需要加強的就是歷史感,而它是以思想深度為內核的。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研究,陳寅恪的傳以代史的研究,無不閃爍著史識、史感的光芒。
史識、史感是通過對歷史及歷史事實的準確評說、深邃評判所得出的理性結論,它往往是不移的、不刊的。在這一點上,21世紀的學術研究者們倒反而要向20世紀的大師們學習。
然而,21世紀畢竟是前進的,在觀念、方法等方面,有超越過去的地方。網絡時代的到來,使得曾經以檢索資料宏富博多而自詡的研究方法黯然失色。然而電腦產生不出思想。就美學史而言,21世紀的美學史研究應該是思想家的美學史研究,應表現為深雋的發現、深邃的解讀、睿智的概括。
真正的史感是什么?20世紀的一些史著并沒有真正解決這一問題,課題留給了21世紀。構合為史感的,是當時性的呈示和歷時性的展示。前者說得過多,后者說得太少。就“當時呈示”而言,也是羅列得多,解讀得少。如何進行“當時呈示”呢?首先要明確的是,所選對象不是某一部美學類別史中的對象,也不能包攬無遺,而是要選擇具有審美代表性和對美學史發展產生影響的對象。所呈示和解讀的,首先應是其美學性質、特征、形態,發掘其審美質素。其次要扣合審美主體的審美心理結構,探究審美性質、特征、形態、審美質素產生的主體依據。第三是探尋審美心態所形成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不同時代的社會、歷史、文化精神不同,所孕育的審美精神也不同。例如六朝玄學與美學、隋唐佛學與美學、兩宋理學與美學。安史之亂帶給唐代社會狀況以至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對詩人們的審美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重的,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杜甫就達不到他現在被公認達到的水平和高度,只能是像高適、岑參那樣的大詩人,而不是“詩圣”。歷史變動對審美變化的影響可謂大矣。但這又取決于歷史大變動的歷史內涵是什么,其容量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兩宋更迭,靖康之難,建炎南渡,宋元易代,明清換朝,給予人們的社會心態進而審美心態的撞擊是巨大的,從而影響其審美性質、特征、形態和質素。這樣就尋找到了審美形態和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的聯結方式和轉換過程,從而實現了有描述、有說明、有現象、有原因的現時性解讀目的。
在歷時性的解讀中,首先要明確歷時性的地位——它更具有史的本體性意義,明確它的兩種發展方式;繼承與變異,或同化與異化。對于繼承、同化,人們說得多;對于變異、異化,人們談得少。而兩者的結合才是歷史延續圖像的完整展示和正確描述。審美意識從產生到發展,構合為審美意識史;審美范疇從萌發到衍化,構合為審美范疇史,其最終體現為審美觀念的影響。影響是前結構的沉淀和沉積,這就是“同化”的體現。另一面則有“異化”。如六朝之于漢是變漢,改變漢的粗獷而至于精約;隋唐之于六朝,清算六朝又綺靡美學之風;宋代之于唐代,在審美格調上改變了唐之博大開闊、沉雄廣放,而現出寧靜自適、淡泊蕭散。同化和異化體現了歷史曲折發展的規律性現象,是歷時性的美的歷程的本體解讀。異化最終體現為心態、心理、心性的變異。唐人感性意識強,理性思辨則稍弱,前不如六朝深刻的思辨,后遜于宋人理學。唐人是詩人,宋人是學者;唐人重感性,宋人富知性,宋人遂改變唐人赳赳雄氣而出現文質彬彬。然而,異化不是直接完成的,需要有中介。初盛唐的中介是張說;盛中唐的中介是杜甫;由唐入宋經過了晚唐體、西昆體的影響和王禹chēng@①、歐陽修等人的反撥性中介,唐音才真正轉變為宋調。所以,同化——異化——中介,才是歷時性演進的完整結構。于是,社會史、思想史凝定為心態史,進而凝定為美學史。
在基本撰述方式上,應以描述與評價、史實與史論、判斷與感悟、思辨與體驗、個案分析與整體把握、實地考察與資料占有相結合。作為美學史更應重視撰述主體的感悟、體驗及實地考察。青銅器、漢畫像、敦煌、麥積山……在實地考察中獲得感悟、體驗、認知等等。美學史的文本文字自然應該是繽紛多姿的,因為對象是美的。把美學還給美吧!心如枯井的撰述心態、筆如枯木的撰述文字,跟美學史是絕緣的。美學史的撰述應該是由一個人獨自完成,以體現個人的學術風采和上述的撰述特色,在這一點上,應向20世紀回歸。也正是這樣才能產生學術名家、大家和大師,否則,只能產生“課題組負責人”。創新是學術的生命和動力,《南齊書文學傳論》響亮地說:“若無新變,不能代雄。”21世紀的美學史研究應以創新為目標,涉及對象、體例、方法、手段等方面。
篇(2)
政治因素無疑對中唐詩壇是最大影響因素。從“永貞革新”到“熙豐變法”,由中唐到宋代均以失敗告終。永貞革新是以改革大歷、貞元以來茍安姑息的弊政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動,故,雖曇花一現,但留在士人們心靈上的希望卻經久耐磨。永貞革新集團的要人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學家,尤其是劉、柳,他們早年熱衷于政治活動,把文學看做余事,但永貞革新失敗后,他們遠貶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們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文學創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補償。因此他們被貶折后的創作,完全是政治上絕望后的孤憤、哀鳴,也有激憤與抗爭。他們的文學成就,是政治與文學互動的結果。柳宗元“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詩風,與劉禹錫“詩多怨刺”的特點,無一不與他們“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關。政治的變化使得文學精神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永貞革新雖然失敗,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還在,因此元和文學就充滿了革新精神,成為中唐文學中輝煌的一段。經歷了甘露之變后,由于文人全身遠禍的心態,整個晚唐文壇反應政治與社會的作品銳減,人們熱衷于對細膩的內在感情的挖掘與玩味,表現個人情感的作品逐漸增多。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賈島現象。
禪宗的發展到了中唐時期,發生了重要的變動。中唐之時,洪州禪一枝獨秀,它所引領的隨緣任運的生命哲學在當時的文士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其思想已經從“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不需時刻想著清規戒律,而是將人性與佛性等同起來,這對于文人參禪風的大興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動蕩,文人命運的未知以及儒學的日漸式微,使得文人士大夫更易選擇佛禪作為自己的精神依傍,以此尋求心靈的超越彌合不得志的遷折人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銘》中寫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②將洪州禪的精神與他素所信奉的老莊道家哲學融合為一,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之中實踐著這一新的禪風。可以說詩文中顯現的這種禪風的駁雜也昭示出當時文人創作時廣征博取、歸于文學本體的發展趨勢。文學在此,向其縱深處探尋出路。
再來具體分析“尚意”的詩學總特征。“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風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③就詩歌的美學理想而言,“四杰”、陳子昂、李白等初盛唐的詩人多追求一種宏闊勁健的美學風格,以抒寫盛世豪情和個人激昂的人生理想。追求魏晉風骨。再從創作機制上看,魏晉到盛唐,更多的強調“感物而動”的即時抒寫與表達。即:自然景色感動了詩人的情感,隨即觸發了詩人創作。而轉入中唐,詩人們開始著意于內心的體悟和韻味的追求,理論也漸趨深微,精致玄遠、以典麗、含蓄為特征。
以皎然的《詩式》為示例。皎然的詩論核心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這是對唐詩和宋詩兩種詩型的整合。將兩極化的表達匯于沉思體味之后的抒寫。這在中唐時期對文人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詩人創作更多的對詩句的傳意效果進行反復斟酌, 在物象的選擇上,也更側重于傳遞內心的一種思緒、積淀。似乎是在波瀾壯闊的盡興之余多了分閉目沉思的體味,讀來更為厚重,沉潛。又如韓愈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這首詩寫早春。攝早春之魂,給予讀者全境式審美體驗。詩人用文學的斟酌之“筆”描摹出早春那種似有卻無的色彩。這是將萬千早春之物象加以提煉的結果。再如元稹“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離思五首·其四》)對于“滄海”、“巫山”的選擇上,選取壯闊深沉的自然物象,以此表達自己對妻子的眷戀和熱愛之深之切。
中唐“尚意”詩學中心論的轉捩意義和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是深遠的。肇始于“中唐”的這種變化,使得文學的關注重心從盛世理想回歸文學自身。削弱功利性的浮夸,增勁審美化的表達。放逐文學宏大氣象的聲勢喧囂,重構文學內部的結構、章法、意境和神韻。《百家唐詩序》中葉燮進一步從宏觀的詩史演變角度指出:“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群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為前后之關鍵矣。”葉燮不僅認為中唐詩苑群才競出,極為昌盛,而且認為中唐是五、七言詩歌發展史上最關鍵性的轉折時期。詩人創作不再是整體的、宏觀的、感物而動、即興而發,而是轉向對意象的提煉、斟酌結合自身創作經驗和個人經歷的再創作,以此縫合自然景物和內心 歷程的裂縫。詩學理論上,皎然的《詩式》力圖矯正大歷詩壇“復多變少”的衰頹局面,以實現詩學精神由“尚情”向“尚意”的過渡。增強了詩歌創作的審美內涵,對文學自身做了一次更為縱深的挖掘。廣義上說,更為唐型詩向宋型詩的變革做了鋪墊。開啟了后世以禪論詩之先河。其后,蘇軾、江西詩派均以此論調,直至嚴羽《滄浪詩話》“通禪喻詩”,以致明代論詩均沿此評鑒。其次,中唐詩歌不斷追求“文外之旨”,將詩道極致立于語言文字之外,影響了后世司空圖、嚴羽、王士禎等,追求“神韻”的詩學理念成為中國詩學史上重要的一支。④從創作論的角度而言,中唐之始對物象的選取,即“取鏡”,更多的講求詩人個人經歷而生成的創作經驗與創作行為的深思熟慮,精心酌取。更多的,是讓文學進一步的向自身窺探,以尋求還原文學性的原貌,打撈文學之精髓。
參考文獻:
[1]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
篇(3)
引言
文學是人格精神和文化成果的集中體現,中國文學就是人格精神和中國文化最藝術、最輝煌的體現。我國古代文學家無一不是人格精神的傳播者和優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作為我國古代歷史上最受群眾喜愛的文學家,李白已經成為一種符號,是符號的指代詞,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文學界限,成為以李白為中心,歷朝歷代學者共同參與和社會公推共享的李白文化。李白文化的出現、存在和發展,反映社會的審美取向和文化認知,對后世文學和文學流派都產生十分重要影響。
一、李白(文化)內涵和內容
1、李白文化內涵
李白不僅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偉大的詩人之一,同時也對世界文化產生重要影響。李白詩歌傳送一千多年不止,傳播范圍十分廣泛,影響十分深淵,是我國古代文學史重要組成內容。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認為,李白是“死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后世學者對李白詩歌不斷總結,產生李白文化,成為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獨有現象。學者何念龍認為,從李白所處的盛唐時期開始,與李白本人及詩歌相關的各種傳說故事,直到今天仍然與李白有關的電視劇和小說等文學作品,構成了歷史異常悠久、內容十分廣闊的文化景觀。在我國數千年的古代文學史上,這是一種極為奇特的,也是絕無僅有的個案。從李白無比輝煌的出生,到去世的巨大影響,以及各地群眾、歷代文人對李白及其詩歌不停的研究、闡釋和傳播,根據個人美學理想和喜好加以重塑和創造,形成了傳播地區廣泛、傳播層面多樣、傳播內涵再創的李白文化。總之,何念龍認為,李白對于我國古代文學史的影響久遠和深遠,的確是無人可比的特例。
2、李白文化內容
李白詩歌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力是無可置疑的,其創作的詩歌、行為方式、思想意識和生平經歷,都是李白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原生體。李白詩歌在其在世期間就已經為人們所吟唱,后世文學家在接受李白、研究李白、尊崇李白、傳播李白的過程中,撰寫大量文學作品,宣傳李白及其詩歌,形成紀念李白的各種民俗文化,稱之為是李白文化。從李白文化的結構層次來看,共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李白文化的物質層次。能通過聽覺和視覺所感知的物質實體稱之為物質文化。李白物質文化主要是指與李白有關的各種遺跡遺跡各地所建造的紀念李白的雕塑、廟宇和祠堂,或者相關戲劇、傳說等。李白在世的時候,一生游山玩水,漫游全國各地,留下大量歷史遺跡。出于對李白的懷念,人們建造了大量的廟宇和祠堂,供奉李白畫像或塑像,流傳李白故事,演繹李白戲劇。后世文人紛紛前往憑吊,又留下了大量詩詞文學作品,歷經千年積淀,逐漸形成具有獨特的李白物質文化。
第二,李白文化的行為層次。全國各地民眾出于對李白的尊崇,定期舉行一些典禮、儀式或廟會,紀念李白。例如,在李白去世之地――安徽馬鞍山當涂縣,每當清明節來臨之際,成千上萬的民眾前往當涂縣青山李白墓進行祭祀。后來,在當涂縣以及李白故里,開展李白文化節日或者吟詩節,成為當地重要文化盛會。
從李白文化三個層次來看,李白精神是李白文化的核心,是李白文化的本質內容,可以說是高層次的不可直接感知的抽象文化部分,行為層面和物質層面則是李白文化的表象。
二、李白(文化)的價值
1、李白(文學)的文學價值
李白在進行詩歌創作的過程中,十分注重文學的審美性,這對于后世學者都具有重要啟示價值。文學的本質是要追求審美,正如李白在其《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言,“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正因為李白是詩歌中具有十分濃厚的懷古情結,使其充滿了境界更為宏大,視野更為開闊,他能夠以一種高屋建瓴的角度和氣勢來觀察人生和現實,在浪漫主義文學風采中增添了理想感、文化感和歷史感。由此可見,李白詩歌充滿跌宕起伏的旋律,充沛的激情,大膽的夸張和神奇的想象,這種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更能夠觸動人的情感,使讀者產生一種感悟、深思和愉悅,把詩歌的自然美也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2、豐富的思想價值
李白留給后人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在他的詩歌作品中,展現了他對于自然和社會的真知灼見,李白文化中豐富的思想價值通過詩歌文學作品得以真實體現,閃耀著燦爛的思想光芒。李白文化真實體現了他在那個時代的胸懷理想報復,但是卻得不到實現的悲觀情懷。同時,李白懷著對祖國山河熱愛之情,蔑視權貴、珍愛生命,其詩作所蘊含的對社會的深入思考,對生活的執著理念,對文化理想的堅守,詩歌內容既深邃,同時也沉痛。這些思想,對于后世學者和文學流派產生重要影響,涌現如歐陽修、蘇軾等文學家,他們不再迎合權貴,堅持自己的理想,堅守自己作品的思想性,從而最終成為一代文學大家。
三、李白(文學)對后代文學家和文學流派影響
總體來看,李白(文學)的卓然獨立的思想個性和偉大藝術成就形成了社會公推共享的文化現象,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蘊含著的鮮明主體精神和強烈主觀色彩,并通過具體而充分的自我表現,深刻、真實反映時代特征。李白在其詩歌作品中,與現實的矛盾沖突、鮮明的個性形象、真實的體驗情感、遠大的抱負理想,共同組成最重要的思想內容。一千多年前的偉大詩人,李白(文學)是我國優秀文化遺產,對于后代文學家和文學流派產生重要影響。
1、李白(文學)對唐代的文學家和文學流派的影響
文章以與李白較為相似的李欣為例,分析李白(文學)對唐代文學家和文學流派的影響。在李欣詩歌作品中,無論是描寫仙道還是憧憬仕途,送別友朋、歌詠邊塞等,大多數都是溫和敦厚,語調舒緩。后來在天寶年間,李欣所作的詩歌,大多數感情深沉、豪放跌宕,特別是對于人物的張揚個性描述,和李白作品詩風是最為接近的。
天寶年間,當李白奉召入京的時候,受到唐玄宗的高度重視,“降輦步迎, 如見綺、皓, 以七寶床賜食, 御手調羹以飯之”,與他仕途追求和思想性格都十分相似的李欣,對此是極為羨慕,“業就功成見明主, 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 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 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莫敢視, 三省官僚揖者稀”。李白杰出的文學才能和傲岸的個性特征、濃厚的浪漫氣質都讓李欣極為仰慕,直接影響他在天寶年間詩風的轉變。由此,李欣在其詩風發生重大轉變,迥然有異,這種轉變可能與他的思想變化以及生活經歷有重要聯系,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李欣受到李白的直接影響。
2、李白(文學)對近現代文學家和文學流派的影響
李白(文學)對于后世文學家,如楊慎、高啟、陸游、辛棄疾、蘇軾、龔自珍、黃景仁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對于現代詩人郭沫若也產生重要影響。1928年,郭沫若在回憶他童年所受到文學的影響時,專門提到唐詩中他最喜歡的是王維、孟浩然、李白和柳宗元,但是卻不是特別喜歡杜甫,更是痛恨韓愈。1941年9月,他在論述詩歌的韻腳和分行問題的時候,就引用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進行闡述詩韻的適度問題,后來他在1961年專門模仿李白的《蜀道難》一詩而創作了《蜀道奇》,作序寫到“李白曾作《蜀道難》, 極言蜀道之險, 視為畏途,今略擬其體而反其意, 作《蜀道奇》”。1962年3月,郭沫若談及他少年時候所受到的影響時強調,唐代的幾位詩人,他最喜歡的是李白。在到訪李白晚年最為鐘愛的采石磯的時候,發出感慨,“李白就是李白, 心胸坦蕩以山動情, 寓江流觴, 真情流露, 毫無偽裝, 詩言其志,蕩氣回腸!” 郭沫若在“五四”時期所作的許多詩歌,在風格和詩風上與李白十分相似,這與他一生對李白的敬仰和仰慕李白,并對李白文學深入研究,汲取豐富營養有重要關系。由此可見,李白(文學)作為我國古代重要文化遺產,影響近現代許多文學家和文學流派。
參考文獻:
[1]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黃群英.李白詩歌的思想內容――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3]彭放.郭沫若談創作[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篇(4)
【關鍵詞】曹植 陶潛 生命意識
Brief talk on the embodiment and comparison of Cao Zhi and Tao Qian’s life consciousness
Gu Weiduo
【Abstract】The poems written by Cao Zhi and Tao Qian, who stand on the Parnassu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Wei and Jin Dynasty, are filled with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The writer has made a comparison and survey on the two people’s different and same life consciousness from three aspects. They both do well out of the humanistic distillation of Chinese archaic Confucian culture,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on their lif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personal tropism, either Zijian’s “advancing” or Yuanming’s “keeping” comes from the personal mod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ach times style and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About the infiltration in their poems, all are full of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and later translated by the later-age Parnassus with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Keywords】Cao Zhi Tao Qian Life consciousness
在我國文學史上,很少有像魏晉這樣思想信仰自由、藝術創造精神勃發、具有大轉變契機的時代。這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于質樸,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統治于儒教;這時代以后――唐代,在藝術上過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而作為魏晉詩壇重鎮的曹植、陶潛則大體上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學上的流動。
1.儒、道傳統文化構架其生命意識。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遭受嚴重的磨難,但同時也是思想特別活躍、傳統文化獲得重大進展的時期。“若論學術思想方面的勇猛精進與開創新天地的精神,這一時期非但不比兩漢遜色,而且有過之。”奠定后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在那個時代,玄學興起,老莊哲學崇尚自然,融匯儒學更新為魏晉玄學,而玄學突破狹隘的倫理道德規范而指向更廣闊的領域,成為個性覺醒的產物,影響了一代玄學乃至一代美學傾向的形成。而另一方面,儒家業已建構的倫理關系由于充滿注重實踐的理性精神,其他各家包括魏晉玄學也無法撼動其根本。
陶潛的思想則單一而雜駁。總體來說,陶詩思維方式帶有冥忘物我、古今混融的風格,而且他的詩文常常只揭示出心中的一隅,這一隅心影中常含有兩極觀念引起的沖突,體現為彼此抗爭又相互融合的全過程,在生命意識方面,陶淵明受儒、道、玄、釋各家影響又與各家皆不同,形成自己獨特的思考。道家是“齊生死”的,主張超世、達觀、順乎自然。陶淵明對生死的焦慮,則既有道家的齊生死,也有儒家的順天命。《歸去來兮辭》中以對生死問題的思考作結: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富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順隨生命的自然變化以了此終生,任性而行,隨心所欲,還有什么可惶惶終日,還有什么可疑慮不休?陶淵明兼用儒道的生死觀,建構自己“乘化以歸盡”的生命意識,升華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2.生命意識在其人格取向上的折射。不同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背景,造就了曹植和陶潛迥異的詩歌風格和人格取向。建安時代士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以建功立業為榮,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偏差,又使他們“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植《與楊德祖書》謂“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全力追求對社會的奉獻與給予中使自身精神人格完善化;“懷我在佐才,慷慨獨不群”是祈望報效國家的真情表白。這種慷慨悲涼的精神貫穿曹子建創作的始終,可見其執著人生,用世心切。而及至陶淵明之時,政治黑暗,由魏至宋長期篡亂不休,不過陶潛“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比阮籍、嵇康自然得多”,這與曹植更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來說,陶潛靜穆,崇尚自然,善解人生而又能應對時代,他有“如此絕世下,六籍無一親”,“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飲酒》)的大惕怵;有“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的大悲慟;也有“嘯寄東軒下,聊更得此生”,“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的大歡喜,始終直面人生,正視現實,他的詩歌即使細小平凡的瑣事也往往系著時代的風云。曹、陶的性格、稟賦及其對人生所持的總體方略,也都不相類。子建熱情如少年,奔放的激情多于沉靜的理智,灑脫盛氣,棱角鮮明,在他身上更多的體現出時代開拓式的熱情啟動,表現出千回萬折的力度。而淵明睿智、圓融、沖淡、不露鋒芒,在他身上更多的凝聚著歷史沉思般的冷峻潛流,體現出百煉化柔的韌性。
3.生命意識在其詩歌中的滲透。曹植、陶潛的詩歌中也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對生命的獨特認識和感悟。曹植和陶潛都是重視生命的,他們的詩文中都洋溢著對生命的體悟與執著。曹子建的詩歌,鏗鏘灑落,氣機旋走,雄逸縱橫,善于抒發慷慨沉郁的奔逸情志,尤其善于表現對外在生命執著不已的豪宕意氣。他珍視生命,也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人生理想,創造不朽的輝煌。因而建功立業是他的詩歌中不朽的主題。陶淵明的詩淡泊寧遠,自然潤和有致,長于抒寫不懈尋覓生命價值的和諧沉思。曹植詩歌時間感緊促急遽,起于積極進取的亢奮心態,“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園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箜篌引》)詩人看到時間的流逝,因而更感到生命的短促。“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游仙》)他渴盼生命的延續,但對生命價值的看法又并非僅以生命本身的永久延續為可貴,而是把建功立業作為生命價值來實現的。他對永生的渴盼,一方面也是由于已身屆人生后期,遲暮之感使他留戀人生,在“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下,零落歸山丘。”(《箜篌引》)的悲涼心情下產生強烈的生命長存的幻想,但這種戀戀之情,絕非對“爵重祿厚”(《求自試表》)作威作福的留戀;也不是對“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箜篌引》)的留戀,在對生命永駐的期盼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曹植這位雄心壯志再度勃發、政治熱情又一次高漲的詩人,假我時日,必有所作為的壯懷激蕩。相對曹植,陶淵明的詩靜怡釋散,寧靜致遠,“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不似曹植時間的緊促,鐫有出自對人生、對社會的冷靜思考。他以一雙慧眼,看透“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擬挽歌辭》)因而“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神釋》)以榮辱不驚、生死不懼的超脫來詮釋自己獨特的生命意識。
宗白華說:“生活嚴肅的人,懷抱著理想,不愿自欺欺人,在人生里面便會遇到不可解救的矛盾,理想與事實的永久沖突,然而愈矛盾則體會愈深,生命的境界愈豐滿濃郁,在生活悲壯的沖突里顯露人生與世界的‘深度’”無論沖突,還是矛盾,曹植與陶潛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生命的堅持。曹植以少年、青年的豪宕,陶潛以成年、老年的睿思,用藝術之筆承載了生命歷程中的掙扎與執著,其詩文中流淌的強大生命意識之流,也代表了魏晉一代士人對生命的體驗,并澤被后世文壇,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 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2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1980
3 《三曹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0
4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篇(5)
京邑賦,尤其是歷代京都大賦,有很強的政治性,它1般都在國家統1穩定時出現。“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文心雕龍·詮賦》),藉對宮殿壯麗、財阜民康、儀禮完備的描寫,宣揚朝廷的功業與威德,起到使4方向慕,人心歸順,加強國家統1安定的作用。班固寫《兩都賦》,背景是東漢王朝建立后,“京師(東都洛陽)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西都長安)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陽之議”(《兩京賦序》),于是班固乃作賦,批評西都的奢侈,贊揚東都的法度,為東都作為穩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強有力的輿論。左思的《3都賦》作于晉統1之后,這時需要有大著作來宣揚作為國家安定統1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蓋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穩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賦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東吳王孫夸贊蜀吳兩地,而代表統1的魏國先生發表宏論,陳述魏都優越,指出冒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于是吳、蜀2家為之折服。從而表現了人們對于3國歸1的認同,這正適合西晉初年的政治需要。《3都賦》之引起轟動效應,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賦對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優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賓襯主,即使對處于賓位的城市,也是以侈麗宏衍之筆,展現其繁盛闊大,因而總體來講,仍然是“極眾人之所眩曜”,顯示出國家之廣大,包含之無所不有。京邑賦除寫帝京、陪都外,歷代還有許多寫地方州郡城市乃至邊疆城邑的。如漢代揚雄的《蜀都賦》、曹魏時劉劭的《趙都賦》、唐代張嵩的《云中古城賦》、明代黃佐的《粵會賦》、丘浚的《南溟奇甸賦》、徐杜的《鄭州攬勝賦》、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賦》。這些,或出于對家鄉風土的熱love,或出于對異地風光的驚異,也是以生花妙筆,寫京都以外州邑勝概。如揚雄《蜀都賦》不僅寫山川的險峻,礦物的豐富,動植的繁多,灌溉的發達,閭閻的密集、紡織的精致,等等,甚至還寫到了川菜的香美,讀之對蜀中的環境和生活,無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賦》則寫了海南島風物的奇特。
京邑賦圍繞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鎮,從歷史到現實,展開多方面鋪寫,內容往往包括歷史沿革、地理形勝、郊甸環境、都市規模、樓臺建筑、動植物產、工商貿易、閭閻風情、宗教禮儀,等等,實為1城1市的綜合介紹與禮贊。這在古代,大大增長了人們的知識,擴展了人們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認識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與資料作用。如張衡《2京賦》除以上提到的1些方面外,還寫到西京平樂館中的雜技魔術表演有舉重、爬竿、鉆刀圈、翻筋斗、走繩、幻術、馴獸、馬戲,等等,成為中國雜技史的珍貴資料。《2京賦》還寫到國際交往,成為外交史上的重要記錄。
都邑賦作為文學藝術中的1枝奇葩,可算出現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學,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藝術美,獲得廣大讀者,同時還以其芳澤沾溉其他文學藝術品種。它對都市的描寫,從謀篇布局、到內容材料、音韻詞藻,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為詩詞文等文體的都市題材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中國文學通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至唐朝時詩取代賦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國勢強盛,未能產生如漢代的京都大賦,但詩為了表現盛唐氣象,卻從漢賦所體現的炎漢氣象中受到啟發。唐京都的長篇歌行,從1定意義上講,是對漢賦的繼承與移植,因而有“賦體歌行”之稱。駱賓王的《帝京篇》、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開頭冒號“山河千里國,城闕9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旨意與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賦完全1致。真是“讀賓王長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燦奪目”。清徐增《而庵說唐詩》云冒號“賓王此篇,最有體裁,節節相生,又井然不亂。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闕離宮,次及諸侯王貴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車馬飲饌之樂,乃至游俠倡婦,描寫殆盡;后半言禍福倚伏,交情變遷,總見帝京之大,無所不有。”所列舉的用鋪敘串合方式展開種種繁華景物,正是京都大賦的寫法。聞1多說冒號“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合的節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4杰》)指明了盧駱的長歌對賦體的吸收。唐詩如此,而到了宋代,寫都市的詞,如柳永《望海潮》詠杭州,王安石《桂枝香》詠金陵,也同樣吸收都邑賦的營養,借鑒都邑賦的寫法。
篇(6)
文學史上對唐詩的分期,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影響為最大,也一直沿用到今,它肇始于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定型于明代高的《唐詩品匯總敘》。“盛唐”一般是指在開元、天寶年間,也是唐玄宗在位時,大致相當于公元八世紀上半葉。這個時期國家統一安定,有相當清明的政治環境,且自武后以后,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逐漸走向完善,實行的是儒、道、釋三教并存的思想體系。盛唐詩歌因此在這樣的社會歷史環境下誕生,涌現出了大批天賦極高、成就斐然的杰出詩人。殷的《河岳英靈集序》中說他們“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在詩體上,既擅長初唐以來講究聲律辭藻的有“新聲”的近體,又擅長抒寫慷慨情懷的古體,并具有“神來,氣來,情來”的氣勢,創造了聲律與風骨兼備的完美境界。
盛唐詩人王灣的一首《北固山下》“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應該是可以概括盛唐時代獨有的盛象。“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以英特豪逸之氣融貫于出色的景物描寫之中,形成雄渾壯闊的詩境。“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自然之美與心境之美完全融為一體,創造出如水月鏡花般不可湊泊的純美詩境。“長風破浪會有時”(李白《行路難》)是一種自信之心,豪壯之氣。李白還以“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的大鵬自比。只有盛唐這樣的時代才能造就李白那樣的詩人,他是天才級的詩人,他的詩歌也是唐詩的魅力所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岳》)表達的是一種寬闊的胸襟,深灝的境界。特別是他的“三吏”、“三別”,雖體現了杜甫的憂國憂民的怨恨之愁,但是這種愁在他的詩歌中表現的是一種宏大之愁、偉大之愁、健康之愁。
以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等為代表的邊塞詩人的詩歌也是構成盛唐詩歌之盛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高適《燕歌行》)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篇》中說:“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高適的詩就是具有這種氣骨、風骨。“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這是盛唐詩人才會獨有的大氣磅礴的胸襟,體現了一種不畏寒冷艱苦的積極樂觀精神。“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出塞二首》)李頎的詩歌也不乏慷慨之音,如他的《古人軍行》“百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等等。總之,盛唐詩,以其對事業功德向往而又廣闊的眼界和博大的氣勢,將唐人重視事功、自信開朗、熱情豪放的風貌淋漓盡致地展現于世人面前。以其熱情蓬勃的感情,激昂慷慨的聲音去表現盛唐時代的種種面貌。盛唐詩歌給人的總體印象應該是:生命意識的覺醒,也是生命之歌的詠唱;是一種自信、進取、豪放精神的激烈;是以玲瓏透徹之心對自然的深沉感悟。
晚唐時期大致是指公元827年到859年,晚唐時期的詩歌氣象,用溫庭筠的《商山早行》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一句概括是較為恰當的了。
唐王朝的衰落已成定勢,反映在詩歌創作上,整個詩壇彌漫著一種濃厚的感傷氣氛,追求藻飾的創作風氣逐漸增濃,憂時念亂或沉迷聲色,隱遁山水,成為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在晚唐,像李白、杜甫、高適等這樣有宏大政治抱負、高度政治激情和強烈政治使命感的詩人,已經幾乎不見蹤影。與盛唐詩人相比,晚唐詩人在政治上顯得軟弱、平庸,他們都逃到自己的個人生活瑣事中尋求一時的快慰,或陷入個人的情感糾葛之中,品咂內心的哀愁和幽怨。晚唐詩人雖然也有牢騷、諷刺和激憤,常常也會帶著一點冷眼旁觀、無可奈何的口吻,也寫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宦場昏暗的社會現實。
就安史之亂以后,晚唐詩人們要分析、總結,有對李唐王朝即將瓦解感到擔憂,又有懷念開元盛世。所以他們往往把感時和論史聯系起來,從懷古引入傷今,詠史(懷)詩大量出現。但是晚唐懷古詠史詩歌的情調與以往的是不同的。像陳子昂與盛唐詩人筆下的懷古詠史所表現的是開拓者的孤獨感和時間的緊迫感交織而成的強烈的責任感,那么晚唐時期的詠古詩則表現為一種冷冰冰的滄桑、挫折感。前者是“壘壘見陳跡,寂寂想宏圖”,是面對歷史而勃發出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后者是“運移漢祚終難復”之感,是一種亂世窮途的絕望和空幻。這種絕望感與空幻感在杜牧、李商隱、許渾、溫庭筠的筆下有不同的反映。“金河秋半虜弦開,云外驚飛四散哀”(杜牧《早雁》)緊密結合時事,深懷著傷時憂民之哀,讀后讓人有一種懷古傷時之感。“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李商隱《哭劉司戶蕢》)抨擊宦官篡權亂政,濫殺無辜,表現了對唐王朝命運的憂慮。“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悵臥遙帷”,(杜牧《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充分表現失意知識分子隔離無依的委曲心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李商隱《龍池》)在對本朝統治者冷諷的同時,寓有深沉的歷史感慨。晚唐的詩歌或以古鑒今,或借古諷今,常常選擇與現實生活具有相似特征的歷史事件或人物進行描寫,或選擇歷史上一些亡國的帝王昏君作為諷刺對象,為當局者提供借鑒,這也是晚唐詠史詩的深刻之處。通常是截取某一特定場景和細節加以想象渲染,以小見大,不著議論而寄意深遠。這種立意方式在晚唐時代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除了內容上的特征之外,晚唐詩在形式上主要運用律詩和絕句,更講究詩歌的技巧工麗,形成綺艷纖巧、純真俚俗的特點,情調纏綿悱惻,語言清麗精工,形成一種“幽艷晚香”之美。 但是以李商隱為代表的晚唐綺艷詩與齊梁之綺麗詩又是迥然不同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晚唐詩的內容寫得純真,格調表現得優雅。其中相當一部分和抒寫人生感慨結合在一起,有的還把傳統的香草美人用比興寄托手法引入綺艷題材,寄托某種政治感受,而并非單純的之作。所以綺艷詩在齊梁和晚唐的兩次回旋,并非重復,而是螺旋上升。它在詩歌的發展史上是一種進步,并對宋詩、宋詞產生了積極巨大的影響。大致說來,晚唐詩歌在作品風貌上給人突出的感覺是:是境界小,骨氣弱的收斂;是政治失意,生活坎坷的悲愴;是艷工整、雕琢纖巧的綺麗;是自我品味,自怨自艾的委婉。
唐詩有不同于其他時代詩歌的總體風貌特征。唐詩內部不同階段,亦如春是秋菊,各有其美,各有千秋,是互不可替代,并且這些不同的階段是呈不斷上升進步、完善的趨勢。唐代詩人苦心吟作,他們豐富的創造性、新鮮的認識感,使唐詩不斷圓熟并臻于完美。中國是詩的國度,唐詩不愧是這國度中最絢麗的一朵奇葩。
篇(7)
1、杜甫草堂概況
杜甫草堂坐落于四川成都浣花溪畔,是唐代詩人杜甫躲避安史之亂入蜀而居時修建的茅屋故居,先后近四年居住生活的地方,于此作許多不朽詩篇賦予草堂深厚的文化底蘊,文學氣息巧妙地與園林景觀相融合,因此仰慕杜甫的世人皆可通過游覽杜甫草堂來紀念詩人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圣地,如今這已成為一所極具價值杜甫紀念遺址。草堂也具有中國古典園林特征。
2、杜甫草堂園林特色及文學感受
2.1杜甫是中國唐朝偉大的詩人,其詩詞歌賦廣為世人所流傳,遺址杜甫草堂如今也成為極具價值的園林,秀麗優雅的自然景觀,以及詩詞歌賦所營造出來的意境美。草堂保留自然美的基礎上,造景充分營造出意境美,游走其中總可以聯想到韻味十足杜甫詩詞,寓情于景。中國古典園林“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征,在此園中得以體現。園中山、水、植物構景要素互相映襯,皆充滿被文學韻味所熏陶。詩詞藝術與風景園林藝術有機融合,游走于草堂隱約感受杜甫詩中的意境,詩情畫意溢于言表。草堂的空間布局也展現了中國古典園林虛實結合意境美的特征,植物配置綠意盎然,虛景實景相互滲透,打造出和諧的局部空間,契合而成令人品味無窮的空間組合。
2.2景觀園林設計多采用變化豐富的曲線來表達,而不是規則直線格局。曲線使園林在布局形式上變得有趣生動。從總體布局來看草堂,景觀豐富,曲徑通幽,園路隨不同園區變化而分布,采用和諧自然的曲線形態,景區之間的空間劃分自然。園內一棵楠樹、一塊景觀石、一條園路、 一片竹林等單個造園要素的分布,錯落有致,都充滿生機。
2.3杜甫草堂既不同于北方皇家園林的沉穩規整,也不同于蘇州園林的淡雅秀麗,它的獨特之處在于營造出詩意的園林空間,古樸自然,寫實寫意相互轉換,園林藝術與作者詩歌畫作相融合,寄情于景,情景之間所表達的人文氣息與意象美。杜甫草堂的山水所營造的意境,也給游人以耳目一新的體驗,文學藝術與自然風景相交融極為契合。草堂布局既體現出了傳統園林的特色,對稱嚴整,優雅穩重,以一條中軸線貫穿始終,由照壁作序景,主要建筑在中軸線上依次呈現,富有層次,營造出多變的空間。通過建立石橋,引水流入,水體潺潺,巧妙的打破中軸線的單一,似斷非斷,使空間更為生動。杜甫草堂的空間形式又不同于傳統園林“序景―起景――結景”的布局,草堂通過空間的呼應與視線的滲透,將融于三個不同意境的詩意空間中,讓游者自然地從莊嚴沉重的神圣空間里逐漸轉變到欣賞優美的園林景觀中。
2.4漫步草堂,遠離了喧囂繁華的都市氣息,仿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清幽僻靜的園林空間。在園中青石板園路縱橫貫通,道旁綠樹相依,點綴著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樓宇亭榭。行走在花徑,竹林小徑,曲徑通幽處;潺潺流水,疊石巒嶂,園路兩旁生生綠意,生機盎然。石板與鵝卵石相拼接的園路,濃蔭蔽地下一叢叢竹林,設有景觀石桌、石凳,可稍作休憩靜靜感受著草堂詩意氣息。寄情于景,娓娓道來,優雅的園林空間使人聯想到杜甫詩詞的文學造詣,在杜甫草堂的審美體驗不僅體現在無限優美的視覺,聽覺、嗅覺感官都會有不同的感染。
3、杜甫草堂的建筑特色
3.1杜甫草堂是詩圣杜甫的故居舊址,是紀念性的空間場所,步入草堂,從影壁開始,花徑兩側的紅墻,由于紅墻的阻隔,營造出一種曲徑通幽的詩意感受。此時的草堂狹長幽靜,薔薇碧竹隨風搖曳。游覽園內特色景觀建筑,杜甫生活過的茅屋故居,建筑內部格局簡單便行,看得到的歷史痕跡,感受到的文人氣息。草堂的茅屋是依據杜甫詩中描寫重新修建的,詩詞“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生動地再現出杜甫當年居住情形。杜甫草堂不僅展現了自然之美,同時意境美與自然美的有機融合營造出了詩意的園林空間,也展現出杜甫的田園生活。
3.2草堂茅屋建筑風格與四川西部當地的民居建筑風格相近,遵循自然,采用川西民居傳統的穿斗結構,不同于傳統祠堂園林的布局方式,屋頂覆蓋茅草,古樸不加修飾,種植竹子,詩意與自然相互交融形成別具一格杜甫草堂園林空間。
4、結論
篇(8)
[中圖分類號]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19-0040-02
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進程中,色彩意象隨著詩歌表現范圍的不斷延伸而逐漸豐富和發展,總體上呈現出一個由簡單、純樸到多樣、繁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這在于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斷提高和心理情感的日趨復雜化以及社會色彩觀念的發展。更進一步來說,人類的認識力和創造力從根本上制約著色彩意象的選取和運用,心理情感的日趨復雜化是色彩意象多樣化的審美內驅力,社會色彩觀念的演變則直接影響著色彩意象的流變。
《詩經》、《楚辭》的色彩較為純樸簡單,多選用青色意象和白色意象,其次是紅色意象、黃色意象和黑色意象。這五種顏色也是中國傳統的“正色”。《管子·揆度》說:“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紅)也。”《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多以自然物起興,如首篇《關雎》中首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展開的是一幅白色流水的青色小島上一對黑色關雎(魚鷹)棲息圖,“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則描繪了青色水草在白色流水中漂浮的姿態。《楚辭》常用香惡草木物象作比,如屈原《離騷》中的白芷、蕙蘭、菌桂、秋菊、菉、葹,等等。這些大多是自然物的色彩直接作用于審美主體視覺的結果,也是先民樸素的色彩觀念的直接反映。
漢魏晉時期的古詩中的色彩意象雖較先秦詩歌有了一定的發展,仍未脫離《詩經》、《楚辭》的色彩選取范疇,而且青、白兩種色彩在詩歌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其中多間雜著形容女子或愛情的紅色意象。《古詩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詩句中的青蔥的意象蘊含的是游子的漂泊不定和思婦的遙望無期;還有像“明月何皎皎”、“明月皎夜光”詩句中,皎潔的月光照出的不僅有閨中女子的空虛無聊,更有寒門士子懷才不遇的憂傷。阮籍的詠懷詩、左思的詠史詩、郭璞的游仙詩以及陶淵明的田園詩仍主要表現青白的色彩意象,但已呈現豐富多樣化的趨勢。
南北朝時期,宋齊時代的謝靈運、謝朓的山水詩,鮑照的樂府詩,色彩意象漸趨多樣、繁雜化。“齊梁以后,形式主義的詩風籠罩著整個詩壇,梁陳宮體詩的流行,更是詩風的墮落”。[3]形式主義的詩風以及宮體詩的流行,從詩歌的精神意義層面上看是詩歌發展進程中的倒退現象,然而從詩歌的表現范圍和色彩意象的發展看,這又是一個必然經歷的成長過程。南朝詩人大多生活在宮廷豪門,或者出于興趣偏好,或者因為身不由己,他們的詩歌內容多表現宮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辭藻艷麗,青、紅兩色是詩境的主色調。典型的代表有陳后主,還有往后的隋煬帝和唐太宗。這些詩人開始將目光從簡單的自然物象更多地投射到社會物象,色彩意象得到極大的豐富和發展。北朝詩歌中的色彩意象的發展則相對緩慢些。由此可見,唐之前詩歌色彩意象總體而言是相對簡單而純樸,這種情況隨著古典詩歌的發展而走向豐富。
中國古典詩到了唐朝達到頂峰,詩歌不僅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獲得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繁榮,因此,唐朝的色彩意象也在這個過程中走向多樣化發展。
初唐時期(618—712年),詩歌色彩意象總體上沿襲了南朝梁陳宮體詩的表達機制,以紅色為主色調,顯得濃艷而缺少深度。“初唐時代,當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齊梁影響的前朝遺老,唐太宗本人對齊梁文風也很愛好。他自己就帶頭寫浮艷的宮體詩、富麗呆板的宮廷詩。他命令魏征、房玄齡、虞世南等大臣編撰《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館詞林》等類書,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供給當時文人們采集典故詞藻之用”。[1]明人許學夷說:“今觀世南之詩,猶不免綺靡之習,何也?蓋世南雖知宮體妖艷之音非正,而綺靡之弊則沿陳、隋舊習而弗知耳。”[2]對于上官儀的詩,史稱“本以詞彩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時稱“上官體”。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初唐詩歌主要表現宮廷生活,對廣袤現實社會缺乏深刻的反映,但還是出現了有別于此的“唐音之始”。[3]如唐太宗、魏征的詩,內容上雖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藝術風格上卻追求雅正,以宏大整肅代替六朝瑣碎柔弱,昭示了唐詩的發展方向和前景。至文章“四友”的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繼上官儀追求辭美,而引向自然流麗。沈佺期、宋之問最終完成了近體詩格律的定型,在詩歌形式上是對辭藻華美、綺錯婉媚的色彩意象的理性拒絕,而內容上仍是沿襲舊制,直至王績和“初唐四杰”奏響了真正的“唐音之始”。王績被認為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先驅,他的《野望》和《秋夜喜雨遇王處士》從內容和風格上是唐詩中“最早擺脫齊梁浮艷氣息的近體詩”。[4]“初唐四杰”之詩,內容上由宮廷轉向市井,由臺閣轉向江山塞漠;風格上由纖柔卑弱轉向流麗省凈,自然清新;感情基調上表現出開朗熱情、積極進取的高亢精神。他們的詩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六朝藻繪習氣,但已有極大進步,色彩意象脫掉了單調的濃艷的南朝華服,逐漸換上了多樣、渾厚而富有內涵的紅黃色彩背景為主,青白意象尤多的盛唐之裝。
到了盛唐(712—762年),景云之后開元天寶年間王維、李白、杜甫、孟浩然、高適、岑參諸公之詩,從內容和形式上都已著上了盛唐之裝,詩歌色彩意象進入了全盛時期。正如嚴羽《滄浪詩話》所云:“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也是林庚先生極力推崇的“盛唐氣象”,本文不必深究。
中唐(762—827年)詩歌隨著安史之亂的沖擊而隨社會走入低谷,隨著國力的衰弱,唐詩中外向、奔放、剛健的時代精神已不如盛唐,而更多地轉向對現實疾苦的反映和心靈的慰藉。“白發”、“青絲”之類色彩意象表現了劉長卿、顧況、韋應物及“大歷十才子”等一批詩人,在沐浴了盛唐之光后面對一個瘡痍滿目的社會那沉痛的歷史滄桑感和生命悲劇意識,這在詩歌色彩意象中有形象的體現。如劉禹錫的名句:“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頭城》),“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烏衣巷》),渾厚色彩背景中是憂國傷懷的濃濃情懷。當然,中唐詩歌雖缺少盛唐外向、奔放、剛健的時代精神,但也不乏沉郁、哀苦,或通俗或怪誕的藝術風格。甚至可以說,隨著詩歌的盛行,中唐詩歌的藝術風格和語言風格的多樣化比盛唐之詩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強烈。杜甫后期詩歌沉郁悲涼的藝術風格已經反映了中唐的社會思想面貌。白居易、元稹等對新樂府的倡導和實踐,使得詩歌由盛唐時的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色彩意象多因淺俗的創作原則的需要又更多地變得艷麗起來,但這種艷麗與初唐時沿襲的六朝靡麗的脂粉氣相比,還摻雜著哀苦無奈的人生況味和時代氣息。韓愈之奇崛險怪、“郊寒島瘦”之苦吟、劉禹錫的優美瀏亮、柳宗元的峻潔騷怨,既是詩人人生境遇的詩化表達,也是中衰社會現實的藝術再現。從色彩意象及其表達機制來看,中唐詩歌全面繼承和極大豐富了盛唐詩歌的色彩意象。我們說盛唐時代是唐詩最高峰是就其精神內涵和藝術表現力而言的,而唐詩色彩意象及其表達機制的全面成熟和最高峰則應該是在中唐時期。
步入晚唐(827—907年),隨著唐王朝的進一步衰落,“盛唐氣象”那種自由奔放的豪氣已經消失殆盡,就連中興希望也變得十分渺茫,詩歌籠罩著哀怨、無奈與沉痛的氣氛。從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最后到晚唐,詩風由浮華的形式主義轉向積極的浪漫主義又轉向冷峻的現實主義,最后落入沉痛的悲觀主義。以“小李杜”為代表的歷史、自然與愛情題材的詩歌,在憂時傷亂、懷古傷今、喟嘆身世之中,流露出精神上的空虛與落寞。而這從另一個方面恰恰促發了他們對詩歌審美藝術的追求,詩歌色彩意象上表現出幽婉明麗的特點。其愛情題材的作品也呈現出與初唐反映宮廷生活的宮體詩一樣的色彩基調,但經歷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滄桑而變得憂郁深沉,不像初唐那般一味的濃艷而沒有深度。自然題材的詩歌,與唐前期的山水田園詩一樣表現出空靈閑適的情調,但不同的是,前期的山水田園詩可以看做是仕途中短暫的消遣和放松,而中晚唐時期的山水田園詩則是于世無濟、醉心自然的逃避和感傷。
品讀唐代詩歌,體悟唐朝思想,不難發現,唐詩色彩意象雖有初唐的浮華而又經中晚唐的靡麗,但終究沒有脫離渾厚雅正的“盛唐氣象”的印象。然而,衰頹的晚唐使得五代詩詞追求形式上的華美,最后興盛了偏離傳統詩道的被稱為“詩余”的文學體裁——詞,色彩意象異常紅艷。而宋、明之詩,受理學思想影響,紅艷之氣漸消,追求理趣,繼而迎來了清詩的中興。可見,詩歌色彩意象的流變反映了詩歌的演變過程,通過色彩意象的流變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詩歌的思想意蘊特征和藝術風格。
[ 參 考 文 獻 ]
[1] 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中國文學史(修訂本)(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19-20.
篇(9)
一、文學審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審美是一種體驗,審美體驗是形象的直覺,外在的客觀之物能通過審美心理機制直接影響并促成審美主體的觀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備的獨特氣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對身處其境的文人們產生特定的文學審美反應。流域之水是一種審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區域色彩后,才復合出其他意象種類。
’
《漢書·地理志》中記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這說明,區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環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區域中,遼河流域主要流經遼寧省、東部地區和吉林省南部地區。以“紅山文化”為代表,主要包括“東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為山高水寒,這使人皮膚收縮,汗毛孔閉合,穿著厚重,與自然的距離加大,對外界持一種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審美態度,故文學上主要選取涼風、寒蟬、白露、飛蓬、歸鳥、孤獸、廖廓之谷等適宜寄托清冷之氣和哀愁、憂患之思的物象,側重冷色調。如完顏亮《驛所》:“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過汝陰作》:“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目暮烏爭噪,幽徑草深入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繞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愛新覺羅·玄燁《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來雨過春濤生”等。
古代文學評論中常把黃河流域所代表的狹義北方文學與長江流域所代表的狹義南方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本文也按此論析。我國秦嶺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長江水系,秦嶺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黃河水系。黃河流域是我國第二大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的約古宗列盆地,流經青、川、甘、寧、內蒙古、陜、晉、豫、魯等9個省(區),東入渤海。黃河流域地理特征為黃土流沙,河寬水湍,是中華文明的先發流域,特別是從漢至唐引領中華文明發展。以“仰韶文化”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趙文學圈、秦隴文學圈、三晉文學圈和齊魯文學圈。黃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導致其民心境開闊,粗獷壯直,憂患意識濃,文學審美上多取狂風大川、巒山闊原、白云駿馬等適宜抒發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傾向于以貞剛之氣敘事辯理,黃色調明顯。長江發源于唐古拉山脈主峰格拉丹東雪山西南側,干流經青、藏、川、滇、鄂、湘、贛、皖、蘇、滬等十個省市。流域內大部分屬于亞熱帶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雨量充沛。長江流域文學以“河姆渡文化”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學圈、荊楚文學圈和吳越文學圈,唐以后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引領者。由于長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險水豐,正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孰饒食,無饑饉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橋、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體現柔、細、雅審美傾向的物象,綠色調突出。古代文學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學的《詩經》和代表南方文學的《楚辭》進行比較,具有顯著的代表性。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里所說:“《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學“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而南方文學“宮商發越,貴于清綺”。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黃河流域文學代表類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氣勢磅礴的漢賦;蒼涼慷慨、風骨勁拔的建安文學;率真爽直、豪放剛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渾悲壯的盛唐邊塞詩;叱咤風云、“挾幽并之氣”的金詞等。如“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操《觀滄海》);“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將進酒》);“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之渙《涼州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張養浩《潼關懷古》)等。長江流域文學代表類型有“信巫鬼,重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學;情辭婉轉、輕靡綺艷的南朝詩歌;潤澤華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園詩;婉約柔媚、徘側纏綿的宋詞等。作品如“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南朝樂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劉禹錫《竹枝詞》);“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憶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諸河四個水系組成,分布于我國的云、貴、桂、粵、湘、贛六個省(自治區)。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嶺,南臨大海,中亙兩廣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間,兼有封閉性與開放性的雙重特點。其代表文學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學、黔貴文學、八桂文學、嶺南文學和瓊州文學,元明清時期才后來居上,成為我國古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一支。文學中多取瘴、嶺、貪泉、毒草、蟒蛇、蠱、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達險惡蒙昧和原鄉審美傾向的物象。具體文學類型有幽怨難適的唐宋流放派;原生開放的明清嶺南文學等。如“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隱《異俗》);“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轉貼于 極,人稱老病馀”(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縱橫。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云生。猿蹈時能嘯,鳶飛莫敢鳴。海窮南徼盡,鄉遠北魂驚。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宋之問《入瀧州江》)等。
二、文學風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學者竹內敏雄把地理環境差異作為影響文學風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國歷代的文學評論者也注重從地理環境角度來研究文學風格,如曹丕、劉勰、司空圖、皎然、姚鼐、劉師培等。
從流域視角來看,遼河、黃河、長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學風格各有特征。遼河流域文學風格以“勁健”、“清奇”為主,帶有鮮明的民族性。文學史上,遼金元時代是遼河流域的興盛期,所以考察這一時期遼河流域文學風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篇(10)
項目名稱:浙江師范大學課程實踐教學項目成果(編號:201129)。
唐代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著名詠酒詩篇《將進酒》,作為具有濃厚探究意義的文學作品,其在文學風格上的審美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文學風格是文體的最高范疇和最高體現,是作家長期匠心獨運的結晶。也正因為如此,讀者往往憑著作品的語言特色,就可以辨別出是誰的作品,把握不同作家作品的風格特點。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語言特色十分鮮明,在遣詞造句上富于奇特的想象,超長的夸張,高度的虛擬,在語言節奏和旋律上則奔瀉急促、迸發突進、氣勢磅礴,這些都體現了其豪放的風格特色。而《將進酒》,就是其豪放風格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豪放風格的審美價值
不同的文學風格有不同的什么價值。雄渾剛勁的風格可以壯人胸懷,清新俏麗的風格可以舒人心脾,飄逸疏野的風格可以養人性情,沉著含蓄的風格可以啟人思力。不同的文學風格,給人以不同的審美享受。《將進酒》豪放曠達的風格特色,也有其特定的審美價值。 段志西說:“李白的《將進酒》一詩具有突出的狂放美特征 ,在作品中主要表現為磅礴遒勁的氣勢美 ,熾烈昂揚的激情美 ,和為了強化氣勢美、激情美而運用的奇譎的想象美、大膽的夸張美 ,從而達到了一種亦仙亦野、傲岸不羈的審美奇境。”
細看《將進酒》詩句“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詩人認為人生雖短暫,但是人活一世,都要盡情把握享受生活每一天。下面兩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它洋溢著詩人自信開朗、清高脫俗的氣質――老天既然讓我來到這個世界,就必定有我的用武之處。即使散盡了千金,也不過是身外之物。只要有才能,這千金還會再回來的。詩句融合著一種對生活自信豁達的態度――所以,趁著現在大家都有這份閑逸的雅致,就要烹羊宰牛大吃一頓,干掉三百杯酒。三百杯當然是個夸張的數字,體現了李白不拘泥、瀟灑的特質,給詩增添了曠達的氛圍。詩人雖然在當時不被重用,但是他并沒有沮喪、一蹶不振,而是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對生活充滿了憧憬,樂觀地享受著人生,體現了其曠達而豪邁的藝術風格。
吳企明曾有這樣一番評價:“詩人想落天外,用兩組排比句發端,突兀驚人,以雄豪奔放的氣概,不同凡響的藝術構想,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群,抒發了自己對時光飛逝、人生短暫的無窮感嘆。”《將進酒》詩句開頭兩句“君不見” 運用夸張的手法,第一句突出了黃河奔流時磅礴激昂的氣勢,而黃河水流入大海不再回淌,就好像時光一去不復返,使人讀后既有一種瀟灑脫俗的情懷,又融入了青春易逝、時光如梭的悲嘆。第二句用了較多顏色的詞匯,如“白”、“青”、“雪”等,形象地描繪出一幅年華易老、人生短促的畫面。其中,“朝”和“暮”、“青”和“雪”構成了對比,早上還是一頭烏絲,晚上已是雪色白發,給人視覺的沖擊,更讓人體會到時間的快速流淌。“黃河之水天上來”、“朝如青絲暮成雪”雄渾豪放,表達出時光易逝的強烈感慨。詩中之歌,乃是神來之筆,敘說古往今來,圣賢不足道,榮華不足貴,富貴功名皆成塵土。最后一層六句詩,宕開一筆,寫出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李白反客為主,連連呼出僮兒,將‘五花馬,千金裘’賣掉,換來美酒,與兩位好友開懷痛飲,長醉方休。結穴處‘與爾同銷萬古愁’,與開端遙相呼應,總結全篇,力敵萬鈞。‘萬古愁’,既指人生不得已之‘愁’,又指我材未用之‘愁’。只有醉酒盡歡,才能消除那深邃廣袤的‘萬古’之‘愁’。詩人將這種愁隨美酒瀉出,少了幾分細膩惆悵,多了幾分大氣磅礴。
縱觀通篇,我們可以感受到其中傳達出來的大氣磅礴的氣勢美,熾烈的激情美和新奇想象和夸張美。
二、豪放風格與時代文化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時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時代氣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學風格必然要滲入時代文化的因素,表現出時代性。李白詩歌的豪放的浪漫主義風格,也與其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李白一生經歷了唐朝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六位帝王,且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隱居和求仙學道的生活中度過的。這種生活培養了他對自由的熱愛,對精神解放的追求,以及不愿受世俗羈絆的性格。他傲岸豪邁又蔑視世俗榮華、向往自由。因此,李白的一生是積極奮發的一生,同時又是坎坷潦倒的一生。
李白所處的時代可以說是盛唐,經濟繁榮,國富民強,因此他少了杜甫憂國憂民、沉郁頓挫的風格,多了豪放豁達、浪漫理想的特點。《將進酒》這首“勸酒歌”, 約作于天寶十一年(752),當時他與友人岑勛到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穎陽山居為客,三人曾登高飲宴。人生快事莫若置酒會友,詩人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蕭士語)之際,于是《將進酒》以自由昂奮的炬火烘映出詩人那昂揚的生命。悲嘆雖然不免,但悲觀不是李白的性格。詩人雖然感到青春易逝,功業未成,自悲自嘆,但另一方面又覺得來日方長,此生大有可為,故又自解,因而“在蕓蕓眾生前行的旅途中留下這一首超越憂傷的千古名曲”。《將進酒》中,詩人所展現出來的悲憤激昂的人生態度和豪放不羈的藝術風格與其所處的時代互相輝映、互相映照,體現了詩歌的豪放風格與特定時代的密不可分的聯系。
三、豪放風格與流派文化
包裹在個人風格外面的,還有流派文化層。流派是一個伸縮性頗大的概念。嚴格地說,并不是每個作家都主動參加過一個明確的流派,但寬泛地說,又可以把大部分作家納入已有的、相關的風格類型,從而認為某某作家屬于某某流派。流派風格的多樣化,往往是文學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唐代詩歌極其繁榮,很大程度上與流派紛呈關系密切,如初唐形成宮體詩派,盛唐出現王孟詩派和高岑詩派,中唐形成新樂府派等。
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也是他的詩歌最鮮明的藝術特色。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調動了一切浪漫主義手法,使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李白的詩富于自我表現的主觀抒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比如,《將進酒》中一開始就運用了兩個氣勢磅礴的“君不見”:“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詩人在詩中將想象、夸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采、瑰麗動人的意境,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韻致的原因所在。
《將進酒》作為李白的浪漫主義特征的代表之一,屬于以豪放飄逸風格為主導的詩派,其綻放出“豪而悲、豪而狂、豪而怒”的獨特浪漫主義風格,使詩歌具有無比神奇的藝術魅力。雖然在文學史上,并沒有明確定義李詩的流派文化。但詩人獨特鮮明的文學藝術風格,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形成了以豪放風格為主導的流派文化。《將進酒》展現了詩人李白的獨特藝術風格,以及其非凡的氣概和生命的激昂。作為一個文學意義濃厚的文學作品,其豪放飄逸的文學風格具有特定的深刻的審美價值。其風格與時代文化和流派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展示了這部文學作品的深遠的探究意義。
參考文獻
[1]劉文晶.試論李白《將進酒》一詩的氣勢狂放美[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9(26).
[2]高建山.一曲生命昂揚的歌――李白《將進酒》品讀[J].現代語文,2005(11).
[3]馬華.從《將進酒》看李白的積極浪漫主義特色[J].中學教學參考,2010(16).
篇(11)
那么這兩種美學的差異究竟表現在哪些地方呢?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種美學所植根的經濟基礎的差異。北方美學植根于北方經濟(以牧業經濟和小麥經濟為主)之上,南方美學植根于南方水稻經濟之中。
二、兩種美學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蘊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較正統,南方的文化則是一種水稻文化,出現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現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兩種美學的精神內核不同。北方以“尚武”為主,并兼有其它多種精神,南方則是以“糜情”為內核。
四、兩種美學所具有的風格的差異。北方美學的風格是豪邁雄壯,質樸淳厚,南方美學則秀麗婉美,浪漫熱烈。
五、兩種美學見之于文藝上也具有很大的差異。正如《隋書·文學傳序》中所言:“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溯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方文藝重于“氣質”,南方文藝重于“清綺”。
這兩種美學的差異性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凸現,如代表北方美學思想的《詩經》和代表南方美學思想的楚辭。袁行霈先生在《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中講到:“先秦時期的《詩經》和《楚辭》就是地域性很強的作品。《詩經》主要是北方文學;《楚辭》則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營養。《詩經》的質樸淳厚,《楚辭》的浪漫熱烈,體現著北方和南方兩地的差異。”⑶但是一開始這兩種美學的地位也并不是對等的,很長時期里,美學一直都是以北方為正統,南方美學遠遠不及北方美學,這種狀況直到魏晉南北朝才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政治上的分裂,北方長時期處于戰亂之中,原本坐鎮北方的統治者及許多北方士族豪門,還有許多北方居民都紛紛南遷,在南方建立國家,開創事業。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⑷正是這政治上的動亂與藝術上的這種精神使得南方美學不斷得到發展,并還出現反超北方美學,一度占據主導地位的現象。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略見一斑:〔1〕從相關著作和研究人才方面,來看,主要是出自南方人之手,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等。在南方出現了諸如劉勰、鐘嶸一樣的杰出人物,而對比之下,北方則要清淡得多。〔2〕在文藝創作人才方面,南方詩人文士占了這個時期的大半個江山,而北方除了由南方去的庾信,王褒外沒有幾個人可與南方相比。那么究竟是發展南方美學還是保證北方美學的正統地位呢?很顯然,南方美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博得了上自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歡迎,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同時南方“猶如在濃厚的脂粉之下掩蓋著貧血的面厐”⑸呈現出一種病態;北方美學雖然一時失寵,但卻是封建統治者維持其統治的強有力的支柱,任何一種揚此抑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然而事實上,很久以來許多的學者文人往往采取一種揚北抑南的方法,隋朝與唐朝初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這種情況。隋朝如李諤、王通等人對南方的文風進行了嚴厲地批評,主張恢復儒家傳統的思想文學觀念,提出了政教中心的文學論。在唐朝初期狐德棻、李白藥、王勃等人也對南朝文風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言:“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官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騖,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但是,還是有一些人在批評南方的時候注意一分為二的方法,主張從南方美學中吸取有用的部分,如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里就反映了這種想法,他說:“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溯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也。”這種想法也正是當時統治者所希望的。
“各去所短,合其兩長”達到“盡善盡美”的結合。要達到這種完美的結合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開明的環境,唐朝恰好是一個相對比較開明的朝代,這種開明不僅僅只表現在政治上,同時也表現在思想文化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個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種思想雜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詩歌,書畫,音樂等多種藝術得到空前的發展;在方面,既有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如道教,也有從國外流傳進來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蘭教等。正因為唐代在思想文化上的開明與多元化,使得唐代詩歌在諸多方面,如思想上,風格上,藝術表現手法上等方面百花爭艷,雖然這種現象并不很久,但是為唐代南北地緣美學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礎。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而且融合了南北兩種不同的詩風、文風,造就了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緣美學的互融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唐代詩歌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對唐代詩歌主旋律的影響。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壯年、中年、老年,唐代詩歌也可以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在少年時期的唐詩,就如“少年心事當拿云”的少年,志高氣盛。到了壯年,則有著一種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中年的時候,直面慘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鮮血有著一種現實主義的精神。到了晚年,國家已衰,亡國之音風起云涌。
首先來看一下初唐時期。這一時期,雖然南方美學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但是還沒有和北方美學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寫到:“初唐時期關中地域繼續受到南朝文學風氣的影響,注重聲律詞采,但是由于關隴文化居于主體地位,所以貞觀詩風呈現出北方化傾向”⑺。所以這個時期的詩歌中的北方氣息相當的濃,其中以“雄渾”、“悲慨”為主,而南方味則要淡以“沖淡”之味而輔之。這個時期出現了如“初唐四杰”和陳子昂一樣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以“尚武”精神為主,氣勢宏大,感情豪邁悲愴。這可以從他們的詩歌中略見一斑。如楊炯在《從軍行》中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閣序》,自然天成,氣勢相當的宏偉磅礴。再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現的雄邁悲愴。而與之同時的,如上官儀等人,他們繼梁陳之余風,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沒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學地位得到了提高,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唐代詩人之中開始了學習東晉南朝的文風之浪潮。如王維學習謝靈運,李白向鮑照、謝朓學習,杜甫從何遜、陰鏗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中寫到:“中間小謝又清發”,把自己與謝朓相比。而北方則出現了如高適、岑參一樣的邊塞詩人。這個時期還是北方美學為主,但是南方美學的影響與初唐相比則有了很大的發展。詩歌的主旋律也呈現出多樣化,有“尚武”的邊塞詩,也有言情寫境的抒情詩,有雄邁宏偉的,也有柔情似水的。總之說來具有“勁健”、“豪放”、“飄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別是安史之亂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戰亂之中,從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許多文人詩客為了避難紛紛南遷,他們不僅帶來了北方的許多文化思想觀念,同時他們也從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營養,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南北兩種美學雜揉并濟推進了南方美學與北方美學的進一步融合,與之同時也使這個時期的詩歌旋律發生了大變。其中如李嘉祐,韋應物,柳宗元等人就是從北方到南方并將南方美學思想用之于詩歌創作之中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大多“纖秾”、“縝密”、“實境”。在大歷年間形成的南北兩個不同的創作群體:一是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如錢起、盧綸、韓雄等大歷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吳越為中心,如劉長卿,李嘉祐等⑻,這就表明南北方已經處于同一個水平層次了。同時也說明了南北地緣美學的互融已經相當有火候。這個時期的詩歌南方味明顯加強,而略少了北方那種鏗鏘有力的感覺了。
二、對唐代詩歌創作群體的影響。
眾所周知,創作主體在作品創作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創作主體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為背景進行創作的,所以創作主體所生存的地域對其創作是有著密切關聯的,所以南北兩種不同的美學思想也勢必會對創作主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唐代的詩人們自然也不例外的會受到這種影響。
在初唐與盛唐的時候,北方過著平靜而有序的生活,同時北方又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產詩人的好土壤,所以這個時期北方的詩人就會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亂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戰亂之中,從而造成了一是許多北方人的南遷,一是南方的開發。這種土壤所造就出來的詩人就不單單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縱觀唐代詩人,據陳尚君先生考證,京畿道有詩人226人,關內道有詩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東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東道77人,山南西道4人,關隴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東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劍南道66人,嶺南道27人⑼。就詩人總體數量來說,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區的詩人增長率遠遠要比北方高。這說明了唐代詩歌的創作群體是一個逐漸變遷的過程。總體觀來,唐代詩歌創作群經歷了一個這樣的演變過程:初唐北方創作群一枝獨秀盛中唐南方創作群的興起晚唐南北創作群的合流。
先看初唐,這個時期的詩人主要集中在關中地區,特別是關中的幾大家族,如韋氏家族,白氏家族,盧氏家族,楊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盧照鄰就是盧氏家族中的一員。而與之相比,南方這個時期的詩人則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時候,北方的詩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韓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時南方的詩人也逐漸發展成熟起來。如張九齡、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詩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時期,南方詩人群更是達到了一個。出現了劉長卿,李嘉祐等人,同時還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創作群體一一吳會詩僧群,涌現了許多的詩僧,據統計盛唐詩僧有43人,中唐詩僧達686人,其中靈一、靈澈、皎然等人比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兩個創作群已沒有很大的區別了,許多詩人已經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來的了。如韋莊,雖出身于關隴,但是卻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黃州,湖州等地做過官⒀。另外,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江南詩僧群,如貫休,齊己等人⒁。
三、對唐代詩歌理論的影響。
受南北地緣美學的影響,唐代詩歌理論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一大批詩人兼理論家。統而觀之,他們提倡“文”與“質”的結合,反對南方詩風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體說來,他們的主張又各有側重。同詩歌創作群的演變一樣,唐代的詩歌理論也是發展變化的。筆者將其分為四個時期:一、端正時期。以孔穎達、陳子昂及“初唐四杰”為代表,主張端正南朝時期的靡糜詩風,回復到儒家大道上來。二、發展時期。以王昌齡、李白、杜甫等為代表,在前者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了儒家詩風。三、時期。以韓愈、白居易等為代表,將儒家詩風推向了一個新的。四、新發展時期。以司空圖為代表,將南北兩種詩風融為一體構成了一個新的詩學體系。
端正時期。初唐時期是詩風的端正時期,其目的就是要從梁陳時期的那種靡糜之中糾正過來回到儒家詩風的大道上來。其中陳子昂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詩歌革新主張的詩人,他指出:“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陳子昂《修竹篇序》)主張向漢魏學習其風骨。孔穎達也在《毛詩正義》提出:“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于言,乃名為詩。”把儒家“詩言志”說發揚光大。
發展時期。盛唐時期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出:“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說。李白也指出:“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李白《古風》其一)主張詩應“清”與“真”,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時期。中唐是唐代詩歌理論一個十分繁盛的時期,把儒家詩風推向了一個新高,其中白居易、韓愈等人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香山集》卷二十八《與元九書》)并指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同上)的主張,把感情和抒事合為一體使儒家詩風進一步與現實掛鉤,而且更具藝術的美。
新發展時期。這個時期之所以為新發展時期主要是意象之說的發展,從中唐到晚唐這段時期里出現了如劉禹錫、司空圖等杰出的詩歌理論家,他們把意境之說加以了發展和完善。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與象進行了區分。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里將詩分為雄渾、沖淡、纖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答莊充書》)之說,而不拘泥于儒家詩學之中。
從這四個演變階段可以看出,其實就是由“風骨”之說到意境之說,于長乎“志”到感于“情”的變遷,這正是北方的“質”與南方的“文”的變通。
唐代詩歌所受到的影響除了以上三個方面,還有其它的方面,這里就不一一例舉。總而言之,從南北地緣美學的沖突與互融之中,可以發現,唐代的詩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兩種美學的互融的渦旋之中,這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唐代的詩人經過了長時期的摸索,把南北兩種美學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裝飾北朝的‘質’,以北朝的‘質’充實南朝的‘文’,創造了中國詩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釋:
⑴⑵《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商務印刷館1940年版第31頁
⑶⑸⑹⒂袁行霈《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第71頁、第22頁、第71-72頁
⑷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頁
⑺尚定《走向盛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
⑻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2頁
⑼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頁
⑽李浩《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9年9月第113頁
⑾⒁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799頁
⑿⒀參見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頁和第196頁
另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