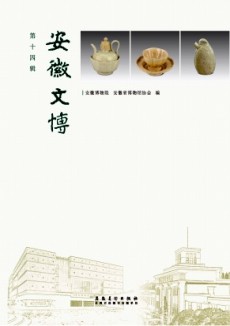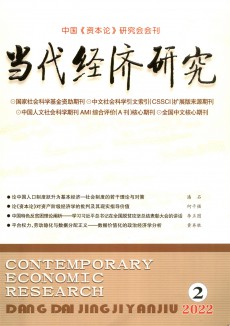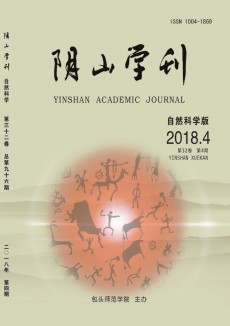關于愛情的現(xiàn)代詩大全11篇
時間:2023-02-05 13:47:16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fā)表云整理的11篇關于愛情的現(xiàn)代詩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fā)。

篇(1)
中國是詩的國度,我們從遙遠的《詩經(jīng)》里走來,從唐詩、宋詞里走來。孔子說,不讀《詩》,無以言。可是,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因此人們認為在這個時詩,已是不可能,是故作姿態(tài)的事。當然,這是極端態(tài)度。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以后,寫詩是野蠻的。奧斯維辛之后,還有人在寫,而且,他把《死亡賦格》,在德國寫得家喻戶曉。這個人叫保羅?策蘭,他這樣寫納粹對猶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殺:“你目睹了那些煙,來自明天”。他的父母和舅舅都死在納粹的集中營……他是繼里爾克之后,最有影響的德語詩人。什么樣的時代都是可以寫詩的。
阿多諾后來收回了他的那句名言,他說,長期受苦難更有權表達,就像受折磨者要叫喊。因此,關于奧斯維辛后不能寫詩的說法或許是錯的。
――是我們還沒有力量與詩歌較量,而不能說,這個時代,不適合寫詩。不能說這個時代,不適合詩,詩適合于任何時代。
沒有人讀詩,這卻是事實。幾年前,我還能找到一些詩刊雜志,這兩年,大街小巷,找不到了。詩歌的荒蕪,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我們?nèi)菀卓吹降膯栴}是,在讀者方面,沒有受到過好的引導、教育和啟發(fā),藝術欣賞的趣味普遍低下;詩歌本身,被翻譯、介紹的作品不多,國內(nèi)寫詩的寥寥,好作品不多。真正好的詩,跟人也是不會隔膜的,是不排斥讀者的。這二者是造成如今詩歌荒蕪不容忽視的原因。我們卻是詩的古國,不缺乏詩的因子與細胞。
朱光潛在《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yǎng)》一文里,很詳細地談了,如何不讀詩的人就藝術趣味低下了。我在這里就不作引用了。雖然他舉的例子,都是傳統(tǒng)詩,但他也提到了新詩,如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等。在欣賞詩歌上,新詩、舊詩,道理是相通的。
說到高中語文教科書上來。現(xiàn)當代詩歌在我們現(xiàn)行的教材中,力量相當薄弱,基本上算是個空白。就算有幾首,也大多嚴重落后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現(xiàn)實,情感、心理、特征,嚴重地膚淺于現(xiàn)實人生,藝術表現(xiàn)粗簡、單一。
記得有舒婷的一首詩《致橡樹》,在那個時代,能夠這樣理解愛情,這樣表達愛情,是有過讓人耳目一新的作用的,她的《神女峰》也是這樣。但這樣的詩,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對情感的理解也好,表現(xiàn)手法的運用也好,就顯得格外地單薄。那樣寫法,說不好,也許只能用來練習寫散文,練習排比的修辭格。
詩之所以成為詩,不是散文,不是議論文,僅僅只有排比句是不夠的。在現(xiàn)代詩那里,抒情甚至是被排斥的。里爾克回答過,“現(xiàn)代詩需要經(jīng)驗不需要感情,感情我們有的夠多了”。現(xiàn)代詩對詩人要求嚴格,想象力,張力,隱喻,暗示,等等。古體詩和近體詩是表達感情,現(xiàn)代詩是用意象羅列暗示情感。好的散文和小說靠近詩,而不是詩靠近散文和小說。
古典詩以“思無邪”的詩觀,表達溫柔敦厚、哀而不怨。現(xiàn)代詩強調(diào)直率的陳述,嚴酷地解剖現(xiàn)實。古典詩是畫筆,現(xiàn)代詩是手術刀。現(xiàn)代詩龐雜,紛繁,含混,于是,現(xiàn)代詩更加地不好言說。――“只有‘距離’能使我的讀者理解我,往往抓住的只是我們之間的欄桿”(保羅?策蘭),現(xiàn)代詩需要這個“距離”。它需要有大的情感跨度和想象跨度。在我所能夠想到的事物中,現(xiàn)代詩跟夢比較接近,它會經(jīng)常違背情理,違背事理,違背邏輯。“你目睹了那些煙,來自明天”。它靈光一現(xiàn)。它的震顫像閃電,從你頭頂上走,讓你措手不及。痙攣和痛苦像死亡。它的吐露像枯枝的排泄。“詩的語言將獲得突然的和精確的亮度”,“他將奇跡般地發(fā)現(xiàn)足夠的想象之島,從島上將飄出歌聲”(杜爾斯?格林拜恩)。
現(xiàn)代詩的意象需要是新穎的、獨特的。
高中課本上穆旦的詩《贊美》和《春》,是我喜歡的。意象紛繁、獨特,表達的精準度和深度,都有。何其芳的《預言》,也不錯。洛夫的《邊界望鄉(xiāng)》,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梁小斌的《雪白的墻》等,是典范作品,但是情感、思想、手法單一了,屬于現(xiàn)當代詩的童年時代。
再有,中學教材中,詩歌的數(shù)量太少。整個高中,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這套教材,只有二十幾首詩,每首都不長。對于培養(yǎng)文學趣味而言,這幾首詩,就是首首精粹,這個數(shù)量也是遠遠不夠的。讀唐詩還要讀三百首呢。
新詩和新小說一樣,并不是我們的傳統(tǒng)劇目,傳入我國的歷史也并不長。可以這么說,對于新詩,現(xiàn)當代詩,現(xiàn)代派詩,最優(yōu)秀的詩人和最優(yōu)秀的詩歌作品,都不在我們這里。不僅我們是后來者,不僅我們又經(jīng)歷文化浩劫,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我們捫心自問,浩蕩的民族,現(xiàn)在有幾人在誠懇地傾聽詩,守衛(wèi)詩?
這里我是要說,我們的高中語文課本,一首外國詩歌都沒有選進來,這是個巨大的空白,空洞,是個玩笑。
我不能從哪個詩人如波德萊爾開始列舉,列舉哪些人、哪些經(jīng)典之作,應該列入我們的教材,世界這么大,他們燦若群星。但他們應該有一個相當?shù)臄?shù)量,存在于我們的教材里,這是肯定的。
還記得里爾克的《嚴重的時刻》,當初是如何讓我對詩發(fā)生興趣的。以下想介紹博爾赫斯的詩――他是一個最不像現(xiàn)代派詩人的現(xiàn)代派詩人――《失眠》。引用這整首詩,也讓我們看一看現(xiàn)當代詩的脾氣、性格,看它們到底跟人、跟時代有沒有隔膜。
夜晚,
夜晚準是巨大的彎曲鋼梁構成,
才沒有被我目不暇給的紛紜事物,
那些充斥其中的不和諧事物,
把它撐破,使它脫底。
在漫長的鐵路旅途,
在人們相互厭煩的宴會,
在敗落的郊區(qū),
在塑像濕潤的燠熱莊園,
在人馬擁擠的夜晚,
海拔、氣溫和光線使我的軀體厭倦。
今晚的宇宙具有遺忘的浩渺
和狂熱的精確。
我徒勞地想擺脫自己的軀體,
擺脫不眠的鏡子(它不停地反映窺視),
擺脫庭院重復的房屋,
擺脫那個泥濘的地方,
那里的小巷風吹都有氣無力,
再前去便是支離破碎的郊區(qū)。
我徒勞地期待
入夢之前的象征和分崩離析。
宇宙的歷史仍在繼續(xù):
齲齒死亡的細微方向,
我血液的循環(huán)和星球的運行。
(我曾憎恨池塘的死水,我曾厭煩傍晚的鳥鳴。)
南部郊區(qū)幾里不斷的累人的路程,
幾里遍地垃圾的潘帕草原,幾里的詛咒,
在記憶中拂拭不去,
經(jīng)常受澇的地塊,像狗一樣扎堆的牧場,
惡臭的池塘:
我是這些靜止的東西的討厭的守衛(wèi)。
鐵絲、土臺、廢紙、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垃圾。
今晚我感到了可怕的靜止:
沒有一個男人和女人在時間中死去,
因為這個不可避免的鐵和泥土的現(xiàn)實
必須穿越所有入睡或死去的人的冷漠
――即使他們躲藏在敗壞和世紀之中――
并且使他們遭到可怕的失眠的折磨。
酒渣色的云使天空顯得粗俗:
為我緊閉的眼簾帶來黎明。
這是一個不祥的、令人不安的鋼梁構成的世界,敗落,擁擠,泥濘,無限重復,有氣無力,支離破碎。垃圾,惡臭,鐵絲,廢紙……人們躲藏在敗壞和世紀中,可怕的靜止,鐵和泥土的現(xiàn)實,遭受可怕的失眠的折磨,連死亡都不被允許通過。
篇(2)
【命題走向】
2000年以前,現(xiàn)代詩歌鑒賞是備受高考命題者青睞的一種命題形式,多以客觀題形式出現(xiàn)。近年來,除部分試卷出現(xiàn)以現(xiàn)代詩歌作為寫作材料或語用部分的仿寫題材料加以考查外,獨立考查現(xiàn)代詩歌鑒賞的試題基本沒有再出現(xiàn)。在經(jīng)歷了十多年的輪空后,尤其是隨著新課標的貫徹實施,《現(xiàn)代詩歌選讀》已成為不少學校的選修教材。在這種情況下,對現(xiàn)代詩歌的考查試題再次登場是極有可能的。在這種趨勢下,該類文本的命題形式將會呈現(xiàn)多樣化趨勢。
【解題鑰匙】
一、品味意象,體會現(xiàn)代詩歌的意境
所謂意象,就是寄托作者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只有抓住詩歌的意象特征,才能較好地理解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所謂意境,就是作者調(diào)動生活積累,運用藝術表現(xiàn)手法,整合各種意象,使主觀的思想感情與客觀的物象相互融合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境界。鑒賞現(xiàn)代詩歌的意境時,首先要對詩歌的直觀形象和畫面進行聯(lián)想和想象;其次要從品味詩歌的語言入手,感悟到詩歌的意韻之美。
一般來說,意境都是由現(xiàn)代詩歌所選用的意象創(chuàng)設出來的。因此,考生在鑒賞現(xiàn)代詩歌時要善于品味意象,從而拓展詩歌的意境。如果不能體會其意境,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進入詩歌所創(chuàng)設的審美世界。如我們所熟悉的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作者面對康橋的自然風光,選取了“云彩”“金柳”“夕陽”“清荇”“柔波”“清潭”“青草”“星輝”“夏蟲”等意象。這些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在詩歌中被作者賦予了自己獨特的感受,這些典型的意象勾畫出了康河的嫵媚動人。
現(xiàn)代詩歌的意象和意境解題技巧:(1)抓住詩中的主要景物,概括景物的氛圍;(2)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抓住意象,把握現(xiàn)代詩歌的情感和主旨
許多現(xiàn)代詩歌在感情表達上秉承了古典詩歌“貴含蓄,忌直露”的特點,作者往往是有話不直說,有情不直抒,而是通過具體意象進行委婉曲折的表達。而現(xiàn)代詩歌的主旨就是詩中所表達的作者的理想志向,所闡述的人生哲理,所蘊涵的美好情操,或?qū)ι鐣θ松v史的總結等。無論現(xiàn)代詩歌的情感和主旨含蓄還是直露,都與詩歌的意象有密切關系,所以領會現(xiàn)代詩歌的情感和主旨要立足詩歌的意象。如艾青的《礁石》就是借“巍然挺立”的礁石形象,表達詩人對被壓迫人民抗擊舊世界暴力的那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的贊頌。
現(xiàn)代詩歌思想感情解題技巧:(1)指出抒發(fā)了詩人什么樣的感情;(2)結合詩歌內(nèi)容加以分析。
三、立足意象,分析現(xiàn)代詩歌的語言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詩歌表情達意的載體。現(xiàn)代詩歌的語言精練,形象,富有音樂美;在詩歌鑒賞中,品味語言是基礎。考生應該聯(lián)系全詩主旨,反復咀嚼,領略詩歌的深刻含義,品味雋永的字詞語句。
下面是現(xiàn)代詩歌關于語言分析的幾種題型的解題步驟,供考生答這類題型時借鑒:
現(xiàn)代詩歌鑒賞詞語解題步驟:(1)解釋詞語的意思;(2)闡述該詞在詩中的作用。
現(xiàn)代詩歌語言風格解題步驟:(1)指明何種語言風格;(2)說出有什么作用。
現(xiàn)代詩歌修辭手法解題步驟:(1)指出何種修辭手法;(2)分析其表達作用。
現(xiàn)代詩歌表現(xiàn)手法解題步驟:(1)指出何種表現(xiàn)手法;(2)闡述其表達作用。
現(xiàn)代詩歌篇章結構解題步驟:(1)指出詩歌結構如何;(2)結合詩歌內(nèi)容作具體闡述。
【針對訓練】
一、閱讀下面的詩歌,回答1~2題。
牽 手
邱彩云
清明節(jié)那天
所有的女友
都被一雙雙大手牽走
只留下我
還有一片哀愁
我也要走
帶上九百九十九朵丁香
放在你的墳頭
陪你到天長地久
因為你曾說
你最喜歡丁香般的姑娘
而你那雙
曾托起溺水女童的雙手
卻再也不來牽我
等待千年顫抖的手
(選自《文學報》2000年11月)
1.詩中的“我”“你”分別是怎樣的人物形象?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試從表達技巧方面,簡要分析這首詩歌。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閱讀下面的詩歌,回答1~3題。
黃河的槳
馬冬生
是從我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的身體里
取出的一節(jié)骨骼。引領我不卑不亢
在混沌的光暈中滾動內(nèi)心的響雷
奔流,奔流,逆風的花朵盛開在最向往的位置
泥沙流動。漫天水色為弦的顫動而顫動
一個旋渦是一聲悠遠而蒼涼的傳喚
黃河的根須在我身體內(nèi)部洶涌
活著的水啊,我能否淘洗出比金子更可貴的東西
歷代的人和事都在奔流,仿佛血在吹
高高低低的命運集結了生的秘密
不是誰都能用黎明的水滌清黃昏的水
強勁的風口,我緊緊握住了什么不愿放開
兩岸猿聲是聽不見了,萬重山擋住歲月的輕舟
我也不知道我將流落到黃河的哪道灣
蒼茫塵世,只剩下一節(jié)骨骼氣壯山河
我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你聽見了沒有
(選自《北京文學》2009年第2期)
1.這首詩歌以“黃河的槳”為題,其象征意義是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怎樣理解“強勁的風口,我緊緊握住了什么不愿放開”這一詩句?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開篇與結尾兩句有什么關系?其寓意是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閱讀下面的詩歌,回答1~3題。
采蓮曲
朱 湘
小船呀輕飄,楊柳呀風里顛搖;
荷葉呀翠蓋,荷花呀人樣嬌嬈。
日落,微波,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右撐,蓮舟上揚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清凈呀不染塵埃。
溪間,采蓮,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拍輕,槳聲應答著歌聲。
藕心呀絲長,羞澀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蠶繭,絲多呀蛹裹中央。
溪頭,采藕,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沉,波升,波上抑揚著歌聲。
蓮蓬呀子多,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喧噪,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采蓬,耳鬢邊暈著微紅;
風定,風生,風蕩漾著歌聲。
升了呀月鉤,明了呀織女牽牛;
薄霧呀拂水,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衣香,消融入一片蒼茫;
時靜,時聞,虛空里裊著歌聲。
(選自《草莽集》)
1.該詩形象鮮明,意境優(yōu)美。作者是怎樣表現(xiàn)少女的采蓮景象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該詩在每一節(jié)的最后都寫到“歌聲”,“歌聲”在詩中有怎樣的作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有人說這首詩的主題是歌頌愉快的勞動生活,有人說是表現(xiàn)愛情生活,你贊同哪種說法?請說明理由。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閱讀下面的詩歌,回答1~2題。
三片葉子
梅紹靜
三片嫩葉像三只綠色的小鳥兒,
驕傲地站在樹樁上。
樹樁只發(fā)出這一條綠莖,
綠莖上只有這三只小鳥。
多可愛的小東西啊,
它們還要為砍斷的樹樁歌唱。
即使只有這三片綠葉也要向世界呼喊,
讓人們永遠憧憬那被剝奪的滿樹春光。
(選自《梅紹靜詩集》)
1.簡要說明這首詩的主旨是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試對這首詩的比擬和象征手法作簡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閱讀下面的詩歌,回答1~2題。
漁 暮
熊召政
這暮色,又被覓草的孤鷺剪亂
慵困的舞翅抹暗了放倒的青山
借與晚風作韻的蓮花
一支支,斜斜地簪出水面
朦朧,亦如湖空冰盤的姣美啊
清香與暮色揉成的江南
小舟從山浦中蕩出了
槳影鋪成的長廊,綠荷正自盈欄
欄外,視線停落的地方
曲曲屏山已不見浮動
船底下,游魚戲逐的浮萍
卻在將波浪的方向交換
(選自《熊召政二十年詩作精選》)
1.這首詩描繪了一幅怎樣的山鄉(xiāng)圖畫?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這首詩題為“漁暮”,是怎樣展開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閱讀下面的詩歌,回答1~2題。
陽光在遠處
艾 青
光在沙漠的遠處,
船在暗云遮著的河上馳去,
暗的風,
暗的沙土,
暗的
旅客的心啊。
――陽光嬉笑地,
射在沙漠的遠處。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蘇伊士河上
(選自《艾青詩選》)
1.這首詩寫于作者遠離祖國,去異國他鄉(xiāng)的路途中。從詩中可看出作者怎樣的心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3)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翻開嶄新的語文教材必修1,跳入眼底的依舊是現(xiàn)代詩歌單元位居目錄之首,收錄的是最經(jīng)典的四首現(xiàn)代詩:的《沁園春 長沙》、戴望舒的《雨巷》和徐自摩的《再別康橋》、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面對教材,心中難免升起種種疑問:現(xiàn)代詩歌并未列入高考考試范圍,為什么卻把它們放在初高中銜接的第一步呢?這幾首詩歌的學習對學生語文能力的培養(yǎng)有何作用?在整個高中階段的語文學習中又有何重要意義?
縱觀高中階段的語文教材,“閱讀與鑒賞”是語文的主體內(nèi)容,收錄的都是名家名篇。不管是對形象性較強的文學作品的品味與鑒賞,還是對思辯性較強的倫理文章的思考和領悟,還是應用性較強的文章的閱讀和理解,目的就是一個:全面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而現(xiàn)代詩歌單元的語言不就是最好的語言學習的范本嗎?所以,筆者就試圖從如何引導學生品味現(xiàn)代詩歌的語言美這個角度,探究詩歌教學對于全面提升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的重要作用。
品味詩歌的語言就是從文字入手,品讀出詩歌語言中蘊含的情感、展示的意境、表達的效果、體現(xiàn)的語言風格。那么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品味詩歌的語言?
1 創(chuàng)設情境,激發(fā)學生興趣
詩歌是抒情的藝術。現(xiàn)代詩歌,情感豐富直白,可利用多媒體手段,創(chuàng)設一個與文章基調(diào)相一致的情境或氛圍,喚起學生的情感需求,帶學生置身于與教學內(nèi)容相應的情景之中,以喚起他們閱讀鑒賞的興趣。如教學《雨巷》這首詩歌前,先播放唐磊的歌曲《丁香花》或《雨巷》改編的歌曲,在纏綿憂傷的音樂旋律中,讓學生初步感受到詩歌營造出的憂郁恬靜的氛圍,教師再深情范讀后讓學生自由誦讀,邊讀邊品味,學生就可以在音樂聲中展開聯(lián)想和想象,就能初步理解詩人的感情及“雨巷”,“丁香”,“姑娘”等意象的內(nèi)涵。
2 知人論世,走進作者心靈
詩如其人。品味語言,不能單純停留在表面,教師需引導學生學會潛入文字背后,走進作者心靈,從創(chuàng)作背景出發(fā),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可以讓學生到圖書館或通過網(wǎng)絡,搜集作家的基本資料、個人遭際、創(chuàng)作背景等,在課上交流。“言為心聲”,了解作者的“心”才能更好品味他們的“言”。如教授《再別康橋》時,筆者讓學生查找關于徐自摩的資料,有的學生找到徐自摩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三位女性的婚戀故事的一段資料,認為他是一個感情極不專一不負責任的人,繼而對他寫的詩也產(chǎn)生了抵觸情緒。有些學生則查閱資料找到了徐自摩思想性格、愛情追求與他的政治理想的密切關系及成因。像“五四”運動前后的新思潮對徐自摩產(chǎn)生深遠影響,他對“愛、美、自由”政治理想的追求等如何表現(xiàn)在詩歌創(chuàng)作和愛情尋覓中。有的學生甚至了解到是康橋蘊育了徐志摩的美好政治理想,理解了他追求林微因,陸小曼的美其實蘊育了徐志摩終生不忘的理想愛情。母校、理想、愛情,就是徐志摩人生追求中“愛、美、自由”的化身。但回國后,軍閥混戰(zhàn)生靈涂炭的社會現(xiàn)實使他的和平自由政治理想破滅。了解了徐自摩這么多,自然就能理解《再別康橋》,能理解詩中徐志摩不僅是在告別母校,也是懷著無奈和心痛告別理想和愛情。
3 反復誦讀、理解詩人感情
古人有“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說法,可見誦讀的作用之大。現(xiàn)代詩歌教學,也應這樣反復誦讀,以誦讀貫穿教學的始終。例如的詞《沁園春 長沙》內(nèi)容是現(xiàn)代的,形式卻是傳統(tǒng)的,押韻、字數(shù)、平仄都有講究,韻律極強。反復誦讀,在誦讀中感受這首詩語言的音樂之美,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再別康橋》和《雨巷》,這兩首詩作為音樂美,語言美的典范之作,教學中,教師可借助聲像資料范讀并指導學生誦讀。誦讀《雨巷》時可播放江南雨巷的畫面,誦讀《再別康橋》時可播放藍天白云、岸邊垂柳、有水草的潺潺小溪的錄像或幻燈片,在伴以輕柔的歐洲田園風情的曲子。在反復的誦讀中,詩意不言自明,語言的內(nèi)涵也能理解。
4 錘字煉句,探究語言魅力
詩歌的語言不僅要反復誦讀,更要仔細品味,推敲錘煉。教師應引導學生注意比較、咀嚼、揣摩,通過抄寫、批注、選詞、填詞、仿句、改句等方式,領會其耐人尋味之處。《沁園春 長沙》這首詩歌中對意象的描摹極其生動傳神,用語精當,極富表現(xiàn)力。一個“萬”字摹出了群山疊嶂之態(tài),一個“遍”字繪出了紅色的徹底,一個“漫”字寫出了江水滿溢之狀,一個“爭”字活現(xiàn)出千帆競發(fā)的熱鬧場面。又如“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中兩個動詞“擊”和“翔”的使用,則可以讓學生通過換字來體會它的妙處。
篇(4)
中圖分類號:I2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2-0036-02
中國詩歌文本的基本單位是“意象”,中國詩歌是典型的意象詩。借助意象抒感成為一種古代詩人普遍采用的表現(xiàn)方法,“抒情詩中運用意象化的最大意義,在于它為無形的主觀情感找到契合的客觀對應物,把不可捉摸的情感,轉(zhuǎn)化為可以感受體驗、理解觀照的形象化的意蘊”①。基于這個原因,中國詩人在創(chuàng)作時,往往勇于翻新,創(chuàng)造出個人化的意象。在某種意義上說,個人化的意象決定了詩歌文本的傳世和詩人的不朽的名聲。意象派大師龐德有感于此,不無賭氣地說:“與其寫萬卷書,還不如在一生中呈現(xiàn)一個好的意象②。”但是,另一方面文學的演變過程中也有一個傳承的過程。詩人在創(chuàng)作時往往不自覺地運用了前人或他人的意象。所以,縱觀中國詩歌史,我們一方面應該看到意象化手法的普遍運用,另一方面也應看清原型意象在古今詩人筆下遺傳變異的情況。以“蓮花”這個意象為例,我們可以從對其歷時性的梳理中反思其在詩歌演變中的變化。
“蓮花”在古典詩歌中既是騷情雅意的寄托,又是愛情的花朵。詩歌中里“蓮”的意象,最早出現(xiàn)在屈原《離騷》“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這兩句詩中的蓮花意象,作為美人香草意象群中的一種,是屈原高潔美好人格的象征。“蓮”意象的騷情雅意,恐怕就肇始于此。在其楚辭作品中我們還可以得到其他驗證,如《湘君》:“采薛荔兮水中,寨芙蓉兮木末”。宋代賀鑄的《踏莎行》:“楊柳回塘,鴛鴦別浦。綠萍漲斷蓮舟路。 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帶雨。依依似與騷人語: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詞中“蓮”的悲劇命運,既是客觀環(huán)境使然,又與自身性格的高潔脫俗有關。其間寄托的美人遲暮的身世感慨,直接承接于屈原騷意。南宋姜夔的《念奴橋》在對荷花盛衰描寫中,亦寄托著詞人懷才不遇、盛往衰來的身世之感和遲暮之嘆。“翠葉吹涼,玉容消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詠荷最為出色,詞人對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情有獨鐘,荷花對品格高潔的詞人同樣意有所屬。在這互為主客的審美交感中,詞人竟覺得不是他吟出了荷花之美,而是荷花飛來化為芬芳的詩句。“嫣然搖動”二句,極見琢煉之功,又極有韻味。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說:“幽韻冷香,挹之不盡”,“藐姑冰雪,蓋為近之”。姜夔對荷花的出色表現(xiàn),影響到了現(xiàn)代新詩人。
余光中《等你,在雨中》一詩中這樣寫道:“你來不來都一樣,竟感覺M每一朵蓮花都像你M尤其隔著黃昏,隔著這樣的細雨”,“步雨后的紅蓮,翩翩,你走來M像一首小令M從一則愛情的典故里你走來M從姜白石的詞里,有韻地,你走來”。余光中這首詩與姜夔相比,除了君子高潔的品質(zhì)之外,多出了愛情的成分。
“蓮”與愛情的聯(lián)系,最早見諸詩歌的是漢樂府的《江南》,采蓮集勞動、游戲、愛情于一體。“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蓮”與“憐”諧音雙關,形成一個模式,被南朝樂府和文人詩歌廣泛接受, “蓮”與“憐”這種愛情表達方式被發(fā)展到了極致,這種狀況我們可以從當時的代表作《西洲曲》中的得到證明。唐代王昌齡的《采蓮曲》是這一模式的延伸:“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白居易的《采蓮曲》卻塑造了一個嬌羞的少女在密密匝匝荷花叢中為欲語還羞得場景:“菱葉縈波荷芰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現(xiàn)代詩人朱湘的《采蓮曲》,則把《江南》模式的內(nèi)容、情調(diào)、藻采,用現(xiàn)代白話的形式加以完整的復活。詩人們在把蓮花賦予愛情的神圣意味的同時,往往不自覺的將之當做心中的伴侶加以描述。比如著名詩人徐志摩的輕柔飄逸的《沙揚娜拉》。詩人將日本女郎的一個微小動作比作“不勝涼風的嬌羞”的“一朵水蓮花”,并沉浸于“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的“蜜甜的憂愁”之中。臺灣女詩人席慕蓉在《蓮的心事》中將自己比作“一朵盛開的夏荷”,希望心中的“他”能夠看到她“最美麗的時刻”,然而,“無緣的你啊!不是來得太早,就是來得太遲”,在愛情的失落中,摻入了時間意識。又如鄭愁予的《錯誤》將思婦的容顏比作蓮花:“那等在季節(jié)里的容顏如蓮花開落”,完全來自古典蓮花的意象,是古代思婦的現(xiàn)代翻版。
古代詩歌中也有一些詠荷詩與騷情雅意和愛情沒有明顯的關系。比如周邦彥的《蘇幕遮》:“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楊萬里的《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詠物寫景,別無寄托。
現(xiàn)代詩人詠“蓮”的詩作也很多,如梁實秋上世紀20年代未曾出版的新詩集《荷花池畔》。新詩中對“蓮”的表現(xiàn),恐怕應以余光中的詩集《蓮的聯(lián)想》為最。該詩集集中收入1961年8月至1963年3月的30首詩,對“蓮”意象做了多層次多維度的透視,詩人認為“《蓮的聯(lián)想》在本質(zhì)上不是一卷詩集,而是一首詩,一首詩的畫面觀”,是“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現(xiàn)代’和受過‘現(xiàn)代’洗禮的‘古典’”,內(nèi)涵“加倍地繁復而且具有彈性”③。余光中的“蓮”是“神、人、物的三位一體”,“美、愛情、宗教”備于一身,綜合了騷雅和愛情的傳統(tǒng),又增加了神性佛性的感悟。它貫通古今,指向未來:“情人死了,愛情常在。廟宇傾頹,神明長在。芬芳謝了,窈窕萎了,而美不朽”,是“美之至,情之至,悟之至”的超時空的存在。現(xiàn)代詠荷詩如周夢蝶的《風荷》、桓夫的《蓮花》、王幻的《蓮曲》、蓉子的《一朵青蓮》、藍菱的《荷塘》、莫渝的《月下讀荷》等,多是美、愛與人生感悟的復調(diào),與余光中的《蓮的聯(lián)想》比較相似。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蓮花”這一意象在古代詩詞中具有騷情雅意和美好愛情的意味,但在現(xiàn)當代詩歌中騷情雅意逐漸脫落,作為愛情象征變得洶涌澎湃。如果把蓮花的這個意象的來源比作一個樹上的大的枝干的話那么,丟失的部分意象則是枝干上被時間的風吹掉的樹枝,代表愛情的樹枝留下了,但代表騷情雅意的樹枝卻隨風而逝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蓮花”這一意象又增加了“美”等諸方面的意義。在漫長的時間里,在詩歌的不斷發(fā)展豐富和融合中這個現(xiàn)象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文化豐富中國傳統(tǒng)意象的同時,“意象化”在20世紀末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新生代詩人公開宣稱:“對語言的再處理――消滅意象!直通通地說出它想說的。”④他們在創(chuàng)作中不再青睞意象、借重意象,而是使用不加提純的口語化的比講究節(jié)制的散文語言還要散漫的日常語言,來如實地記錄他們瑣碎卑微、本真的日常生存狀態(tài)。這種被于堅稱為“拒絕隱喻”的表達方式完全顛覆了意象的表述方式。加之被布魯姆稱為“影響的焦慮”的心理的存在,一些詩人在“消滅意象”的前提下上演了一場群魔亂舞的語言狂歡,將傳統(tǒng)的意象完全淹沒。至于“蓮花”這一意象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在尚存爭議的歌詞中倒是出現(xiàn)了一些關于“蓮花”這一意象,比如《心如蓮花開》等等,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蓮花”這一意象在民間尚有一定的市場。
錢鐘書在《談藝錄》八二及補證中,引用大量精辟論述,充分說明“詩雖新,似舊才佳”是一條古今中外皆同的審美通則。這對于新詩創(chuàng)作和批評鑒賞具有意味深長的啟示:新詩如何走出一條繼承傳統(tǒng)的“通變”發(fā)展道路,以適應我們民族在漫長而又燦爛的詩歌傳統(tǒng)中形成的異常深厚的文化心理積淀,讓新詩贏得更廣泛的讀者。作為在詩歌長河中沉淀下來的古典意象如何在新的語境中煥發(fā)出新的生機,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蓮花”這一意象不應也不會在詩歌中凋落,而應在詩歌的演變中開出它的新的風致。不過,我們從“蓮”這一角度尋找我國審美意象變化的軌跡的時候,不能不同時顧及到這一意象普遍表現(xiàn)著古代趣味和現(xiàn)代趣味的糅合。
注釋:
①楊景龍.古典詩詞曲與現(xiàn)當代新詩[M].河南:河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
篇(5)
引言
中國在兩千多年來的翻譯史中不僅推出了許多翻譯巨著,而且關于翻譯的理論和觀點也層出不窮。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的標準一直是翻譯大師們討論的焦點。因為文學翻譯不只是文字符號之間的轉(zhuǎn)換,而且是文化觀念的傳遞與重塑,所以文學翻譯是翻譯之難點,而詩歌翻譯又是難中之難。許多中外文學家和翻譯大家甚至至今還在討論詩歌的可譯性和不可譯性。詩歌不可譯性是指,很多翻譯家認為中國的詩詞曲不僅在詞句上有許多文字游戲的應用,而且具有嚴格的韻律。因此,如果外國人想要領略中華詩歌瑰寶的全部光彩,就只有親自拜讀原文了。而另外一些人認為,詩歌不是不可譯,而是當今社會缺少可以翻譯詩歌的大家,確實如此,讀者在現(xiàn)有的詩歌譯作中仍然可以不斷看到非常絕妙的譯本。這些譯作無論從詩的形式還是內(nèi)容方面都譯得很美,可謂達到 “形與神共似”的果效。那么一部詩歌譯作如何才能做到“神形共似”、真正忠實原文呢?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將借助一首中德詩互譯的例文——歌德的《米麗容歌》的兩篇譯作比較,來說明什么才叫做忠實原文,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忠實原文。
一、翻譯標準之多元等價論
自從翻譯這一行為存在的那一刻開始,有關翻譯標準的爭辯也未曾停止。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各個翻譯名家分別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翻譯標準學說,三國時的支謙提到的“循本旨,不加文飾”①,東晉道安所倡的“案本”②, 唐人的“信”③,以及近代嚴復所提的“信,達,雅”的“信”④, 朱生豪的“神韻”說⑤,傅雷的“神似”說⑥,錢鐘書的“化鏡”說⑦等,以及國外譯論家的類似提法,如英國泰特勒的“三原則”⑧,巴阿爾胡達羅夫的“語義等值論”⑨,美國奈達的“等效”論等,所有這些提法文字上雖然有別,但它們所表達的思想內(nèi)容都一樣,即,翻譯要忠實原文。國內(nèi)外翻譯家們將這些理論又稱為多元等價標準論,即把翻譯的各類標準集中起來,建立成多元互補標準。我國當代著名詩歌翻譯家辜正坤先生將此標準總結為:譯者應從語言、文體、文風、翻譯場合四個方面做到原文與譯文全面等價。具體來說,語言等價又包括五點:1.語音標準,2.字法標準,3.句法標準,4.語形標準(指字、詞、句的書寫及排列形式,如詩行排列形式等),5.語義標準。從文體形式的角度來看,譯者也應從一下兩方面厘定標準:1.藝術性文體翻譯標準(如詩歌、抒情散文、小說、戲劇等);2.普通敘述文體翻譯標準(如歷史文獻、普通敘述文之類);3.科學技術著作翻譯標準;4.抽象理論著作翻譯標準(如哲學、美學文獻等);5.應用類文體翻譯標準(如契約類法律文獻、申請、報告等)。文風等價包括譯文與原文應保留一致的文風,即樸實的文風;華麗的文風;雄辯的文風;晦澀的文風;明快的文風。此外,譯者還需從特定的場合因素角度厘定標準:1.學術標準,2.娛樂標準,3.政治功利標準,4.臨時性應用標準, 5.其他標準。
二、借助譯作分析多元等價論互補在詩歌翻譯中的必要性。
接下來,筆者將通過對德國詩人歌德《米麗容歌》(Mrignou)⑩的兩個中譯本的比較來說明多元等價標準互補的必要性。首先,從純語言的角度來比較兩篇譯作:
詩歌翻譯其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音節(jié)的押韻。從歌德的《米麗容歌》原作中可以看出偉大詩人的這首詩有嚴格的韻腳。其每兩句的句尾都以同樣的韻尾結尾,即:如一二行中的“blühen”與“glühn”中的ühn,以及三四行中的eht,二節(jié)中的ach,an 等。然后我們看兩篇譯文,馬君武先生的譯本是一首七言雜體詩,他的譯文每節(jié)也有嚴格的韻尾:第一節(jié)整節(jié)都用的是iang這個音節(jié),如,“xiang” (鄉(xiāng),香),“huang”(黃),“l(fā)iang”(涼)。第二節(jié)基本上以an 為韻腳。 而錢春綺先生的譯文中雖然也有押韻,如一節(jié)一二行尾的“fang”(放)與“guang”(光), “feng”(風)與“song”(聳), 但是沒有馬先生的譯文韻味更加鮮明。錢譯本與原文的相似是兩行兩行進行押韻, 而馬譯本則是每一節(jié)的每一行都押同一個韻。相比之下,雖然錢先生形式上與原文更加接近,但馬先生的譯本讀起來則更符合中國讀者的習慣。
從語法,即,詞法和句法的角度來看, 由于德語與漢語是兩種擁有不同語法體系的語言,所以無論從詞法還是從句法都很難做到等價。如此詩的第一段,每一行都以動詞結尾,而兩篇譯文:馬先生的“黃”、“涼”、“香”雖然是形容詞,但也是很形象的體現(xiàn)了原文所表達的動作。而錢春綺先生則運用了“閃”“吹”“聳”等詞,從詞性上來看很符合原文,而且都用的動詞,但是被放在了句子的中間, 運用了漢語簡單句句型:如,“香橙在綠蔭處閃著金光”。從原文來看,作者把地點說明語放在句首則有作者的用意——強調(diào)。這樣看來,如果在語法上不仔細、反復推敲作者的寫作意圖,譯文就會失去原味。
語形標準是指詩行的排列形式。馬譯本是七言為主的中國式古體詩。譯者運用了中國古詩和民歌中連章半重體的形式,如詩歌開頭的“君識此,是何…”以及每節(jié)結尾的“歸歟!歸歟!愿與君,歸此…”。這種表現(xiàn)形式與原詩每章首句尾句的反復吟詠基本符合。錢先生的譯文則是白話文的現(xiàn)代詩。句子結構及字數(shù)都沒有嚴格的規(guī)律。但他的節(jié)首與節(jié)尾也都與原文對應,也有重復出現(xiàn)的句子,如,“你可知道那地方”、“前去,前去”。
從語義等價原則來看,選詞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精挑細選的過程,在詩歌互譯中,不免會碰到譯入語中壓根找不到與原文相對應的名詞或表達方式。這就給詩歌翻譯帶來了更大的困難。例如,原詩中的Mytre本來是一種桃金娘科,而且它是象征愛情的維納斯的神樹,Lotbeer是指月桂樹,是太陽神阿波羅的神樹。 馬先生分別把它們譯成了中國人可以理解的沒藥和桂花,錢先生則進行了直譯。二者相比后者的譯文與原文在意思上等價值比較大。 但其整體效果卻不及前者。試把“桃金娘悄然無語,月桂高聳。”與“沒藥沉靜叢桂香”比較,總覺得后者更像歌德的詩一些。
由于筆者在此比較的是詩歌翻譯,所以其比較的范圍就局限在特定的方面,除了從純語言方面,筆者還將從文體和文風兩個方面簡單的對其進行比較。總的來看,其文體形式都是藝術性文體,而且兩篇譯文也都是詩體。但馬先生的譯本更符合歌德原文的文體,因為歌德所用的是格律比較鮮明的文體,馬譯本則貼切地運用了中國的古詩行。而錢春綺先生譯成了比較自由的現(xiàn)代詩,與原文的詩體不大一致。從文體風格來看,兩個譯本都是比較晦澀的文風,從譯文中讀者也能感受出迷娘當時復雜的心情B11。
結語
詩人、作家、翻譯大師郭沫若曾說過:“好的譯文等于創(chuàng)作”,通過上面對兩篇譯文的比較,筆者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錢先生的譯文在語義方面比較等價與原文,而馬先生的譯本雖然在詞字的具體意思上沒有等價與原文,但他從語音,語法,即字詞的位置的安排,詞性的選擇,整首詩的語形、語體、文體風格則與原文的等價度更大一些。雖然兩個譯本都是詩體,但是中文讀者讀后感覺馬譯本更像一首“歌德詩”。因此,通過兩種譯本的對比使讀者與譯者產(chǎn)生如下啟發(fā):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必須多個等價標準同時共同作用,不能只從單個等價標準入手,而應將純語言標準與文體文風標準多元結合,互相配合達到形與神共似的最高境界。為了達到這點,譯者首先應把原文的詩體形式保留下來,即,古詩就應被譯為古詩,并且進行嚴格的押韻;因為如果把古詩譯成現(xiàn)代詩,或是把現(xiàn)代詩譯成古詩,都會造成詩體形式上的不等價,比如說把歌德的詩譯成現(xiàn)代詩,那么就會使讀者造成以下誤解:讀者以為德國中世紀的人不會做韻文詩;德國從那個時代開始就說的是當代所用的“白話文”,或者詩體的不等價使原文的意味就有幾分失色。所以譯者當以原文本為出發(fā)點,使讀者、譯者和作者三者之間的心理等價值增大。詩歌譯作要是沒有了意境,就等于把詩給毀了,要是單純?yōu)榱俗屪x者能看明白,那么譯者在譯古體詩時應該加上解釋的語句,如:“某某詩的白話文版、古體詩版、兒童版…” 或可以加個注釋,如,“此文是某某詩的釋文”等。好比有人把《論語》譯成白話文德語一樣,應當注明原文的文體。
參考文獻:
[1]孟昭毅 李載道 主編 中國翻譯文學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2]辜正坤編 中西詩比較鑒賞與翻譯理論[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
[3]汪榕培 比較與翻譯[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
[4]王金鈴 文學翻譯新論[M]作家出版社1995年5月
[5]郭廷禮著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6]黃國彬編 因難見巧——各家翻譯經(jīng)驗談[M]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96年香港有限公司
[7]李新樂著 文學翻譯的藝術哲學[M]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8]歌德著 錢春綺譯 歌德詩集上[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9月
注解
①支謙:《法句經(jīng)序》,《三藏記集經(jīng)序》卷七。
②道安:《錃婆沙序》,《三藏記集經(jīng)序》。
③魯迅:“唐人以‘信’為主,粗略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見魯迅《二心集》
④嚴復:《天演論譯例言》:“譯事三難:信達雅”
⑤朱生豪:《莎士比亞全集譯者自序》:“朱譯此詩的宗旨,第一在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nèi),保持原作之神韻”。
⑥傅雷:《重譯本序》(1951):“以效果而論,翻譯應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⑦錢鐘書《林紓德翻譯》:“文學的翻譯最高標準是‘化’”。
⑧三原則即:第一,譯文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第二,譯文的風格和筆調(diào)應與原文的性質(zhì)相同,第三,譯文應和原作同樣流暢。
篇(6)
第二,要進行開放式的解讀與賞析。解詩中所說的“詩無達詁”,并不是說喪失標準任意而為,而是說對于一些具有豐富復雜內(nèi)涵的詩歌可能會有多重解釋,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力求找到最符合原意的“可能性”解讀,這是靠近式的解讀,而不是遠離或僵化的就詩論詩。筆者以為,這種開放式的可能性解讀首先應該是一種深度而準確的講解,不能只是泛泛而談,更不能是離題的解讀,而應是一種“細讀”。這就需要考慮到時代背景、歷史現(xiàn)實和文化內(nèi)涵等因素,以及字句中復雜幽微的意蘊,當然,豐富的軼聞史事也可以從旁充實。比如聞一多的《色彩》,這首詩寫的雖是“色彩”,其實是在寫“生命”,“色彩”的豐富多彩(紅黃藍黑等)就是“生命”的豐富多彩(愛恨生死等),關鍵的詩句是“生命是張沒價值的白紙”,“從此以后,/我便溺愛于我的生命,/因為我愛他的色彩”。就我所知,有些教師對這首詩的解釋很膚淺僵化,居然讓學生把各種色彩對應代表的意思背會,考試中居然會給出“紅黃藍黑”各代表什么意思的考題,想到學生在“綠――發(fā)展、紅――熱情、黃――忠義、藍――高潔、粉紅――希望、灰白――悲哀、黑――死”之間劃上對應號,我覺得這樣的詩歌教學是失敗的。其實,對這首詩在色彩上的隱喻運用,教師也可以結合聞一多繪畫的功底講講他詩歌中的繪畫美,也可以講講色彩的主觀性。而現(xiàn)在有些教師往往把一些飽含情感、極為感性、意味無窮的詩歌給程序化了,把傳達豐富細膩感情的靈性美簡單化為枯燥無味、死記硬背的符號,恨不能把學生的大腦當做一個知識的硬盤全部拷貝儲存進去,而思想的深沉、語言的美感、情感的撞擊、精神的愉悅等等都被稀釋掉了。所以深度準確的解讀應放在第一位,不是淺顯的闡釋,更不能是離題的闡釋,或是斷章取義、只顧字面意思的解釋。
開放式的解讀不等于隨意的解讀,而是切近原意的解讀,所以應盡量減少曲解原意的誤讀。比如對于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首詩的講解,就不能簡單停留在詩句表面,而應結合詩歌創(chuàng)作背景、詩人的文化心理進行分析。這首詩語言明白如話,意象單純明凈,詩風清新明朗,全詩基本是以質(zhì)樸明朗的筆調(diào)和直抒胸臆的情感剖白為主,表達詩人對塵世幸福生活的憧憬與棄絕,以及對理想生活執(zhí)著而孤獨的追求。詩中比較好理解的是對得到幸福的喜悅和對塵世中親人、友人以及陌生人的祝愿,流淌著一種溫暖清麗的氣息。但是這首詩人自殺前兩個多月所寫的作品,看似單純、平淡,卻寄意幽深,溫婉平和中透露出詩人對都市物欲生活的拒絕和對鄉(xiāng)村純凈生活的向往。“大海”構成詩中的核心意象,成為詩人理想的象征和靈魂的皈依,詩人的一切向往和全部的人生理想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全詩最關鍵的、最能泄露詩人內(nèi)心秘密、反映詩人最真實感情的是最后一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是詩人情感與生命的最終歸宿。詩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塵世中的幸福”與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幸福即“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在根本上是異質(zhì)的,是無法相合的,言外之意是:我自己不在塵世,塵世的幸福不屬于我,是給予別人甚至陌生人的,因為,“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詩人把美好的希望和祝福留給塵世,而詩人自己追求的幸福卻是超越棄絕了塵世幸福的永恒幸福。全詩有幾組隱含的對比關系:人物關系是“你”(“我”之外的塵世中人)與“我”的對比,“從明天起”暗含的是時間關系上“明天”與“今天”的對比,在精神追求中,“塵世”代表的“現(xiàn)實世界”和“世俗世界”暗含的是與“理想世界”的對比,對比關系使海子的詩歌意蘊顯示出一種悖逆色彩與雙重意蘊,在詩中交織成一種理想與現(xiàn)實、瞬間與永恒、單純與悲傷、寧靜與絕望,祝福與棄世交織的情感張力,這正是這首詩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所在。
第三,要注意運用歸類、比較等多種方法進行教學。教師可以把授人以魚與授人以漁的方法相結合,從各種角度比較不同詩歌作品的共性或相異的特征,從主題角度、性別角度、歷史時代文化角度,以及詩歌構思的方式,提供一種立體式、多角度而非單一化的解讀方法。比如,同樣是愛國主題,講艾青的《我愛這土地》、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和舒婷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應是不同的,可以比較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不同的詩美詩意,而共同的地方又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又如,在講解余光中《鄉(xiāng)愁》和席慕容《鄉(xiāng)愁》時,可以讓學生比較、總結從古到今中國詩歌(文學)中的“鄉(xiāng)愁”主題,并體會“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普遍情感,教師可以與古代邊塞詩與田園詩相比較,把現(xiàn)代詩人與古代詩人李白、高適、陶淵明等比較,從鄉(xiāng)愁意識擴展到人類的歸鄉(xiāng)意識、鄉(xiāng)土情懷和家園感。
一個作家的其他詩歌作品既可以作為擴展閱讀,也可以作為比較閱讀,教師最好能加上詩人同時期創(chuàng)作的另一些同主題詩歌,或者不同詩人在不同時期的同主題詩歌。仍以“鄉(xiāng)愁詩”為例,講余光中的《鄉(xiāng)愁》時,可以加上他的《鄉(xiāng)愁四韻》、《民歌》作為擴展性閱讀,這兩首詩無論在形式、結構、音韻,還是在詩歌技巧、修辭手法上都與《鄉(xiāng)愁》有異曲同工之處。也可以給學生介紹、閱讀其他詩人的一些鄉(xiāng)愁詩名作,如臺灣詩人洛夫的《邊界望鄉(xiāng)》與鄭愁予的《鄉(xiāng)音》,朦朧詩人舒婷的《還鄉(xiāng)》和現(xiàn)代詩人卞之琳的《鄉(xiāng)愁》等。在把“鄉(xiāng)愁詩”主題的詩歌歸類之后,再對其思想感情、寫作技巧、形式、修辭手法等進行異同的比較分析。
篇(7)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詩的國家,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詩經(jīng)到“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的現(xiàn)代詩,這其中有快樂,有傷離;有愛情,有友誼……但不變的始終是詩香四溢,詩意的人生。
歷史的帷幕緩緩打開,我看到了一幕幕關于詩的決美篇章……
在汩羅江邊,楚大夫沉吟澤畔,九死不悔。屈原面對國家的衰敗,面對同僚的嫉妒,面對學生的背叛,他沒有悲觀,而是以一位詩人本擁有熾熱的心與黑暗勢力作斗爭。最終吟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豪言。這使我感動,讓我明白,在何時,遇到任何困難,只要有一顆堅定的心,并不斷奮斗,就能戰(zhàn)勝困境。
來到東晉的深山,看到一位智者在躬耕隴畝,他就是陶淵明。陶淵明,在這黑暗的社會中,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為保持自身的人格尊嚴,歸隱田園,放棄了世俗的喧器,呵護了守靜,不然怎么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優(yōu)美詩句流傳后世。這震憾了我的心靈,讓我懂得有時也應放棄紅塵的喧雜來擁抱自然,讓身心沉浸在自然的和諧與靜謐中。
在黃州,蘇軾回想著仕途的坎坷,遭貶的不幸,面對昔日赤壁戰(zhàn)場,突然胸懷變得舒暢,吟出“大江東去,浪淘盡。”的名句,從此他又樂觀地對待人生,在黃州興建水利,為民造福,做出許多對人民有利的事。“小舟從此逝,滄海濟余生。”這讓我理解了原來任何的磨難都是小事,只要我們以微笑去面對,就會看到鷗翔魚游的水天一色。
面對朋友的離別,王勃高唱“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面對關場的打擊,李白放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面對生與死的決擇,文天祥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漫游在這詩的國度,感受著詩香四溢,覺得自己的靈魂得到凈化,精神得到升華。
與詩交流,詩意人生,令我沉醉與向往!
有詩相伴
無論是春光乍現(xiàn),還是秋水波瀾,無論是夏花掩目,還是雪映庭院,如果生命有一日,我便讀你一天,晨,手捧朝霞伏案;午,細品陽光絢爛;夜,解讀銀河星漢。有你相伴,我便不會孤單。
有詩相伴,便有自信相伴。我可以從“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中揚起自信之帆,我可以從“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中撐起自信的長蒿,我也可以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到自信之舟,我還可以從“處士禰衡俊,諸生無縣貧”中尋到自信的支點。
篇(8)
歷史的帷幕緩緩打開,我看到了一幕幕關于詩的決美篇章……
在汩羅江邊,楚大夫沉吟澤畔,九死不悔。屈原面對國家的衰敗,面對同僚的嫉妒,面對學生的背叛,他沒有悲觀,而是以一位詩人本擁有熾熱的心與黑暗勢力作斗爭。最終吟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豪言。這使我感動,讓我明白,在何時,遇到任何困難,只要有一顆堅定的心,并不斷奮斗,就能戰(zhàn)勝困境。
來到東晉的深山,看到一位智者在躬耕隴畝,他就是陶淵明。陶淵明,在這黑暗的社會中,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為保持自身的人格尊嚴,歸隱田園,放棄了世俗的喧器,呵護了守靜,不然怎么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優(yōu)美詩句流傳后世。這震憾了我的心靈,讓我懂得有時也應放棄紅塵的喧雜來擁抱自然,讓身心沉浸在自然的和諧與靜謐中。
在黃州,蘇軾回想著仕途的坎坷,遭貶的不幸,面對昔日赤壁戰(zhàn)場,突然胸懷變得舒暢,吟出“大江東去,浪淘盡。”的名句,從此他又樂觀地對待人生,在黃州興建水利,為民造福,做出許多對人民有利的事。“小舟從此逝,滄海濟余生。”這讓我理解了原來任何的磨難都是小事,只要我們以微笑去面對,就會看到鷗翔魚游的水天一色。
面對朋友的離別,王勃高唱“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面對關場的打擊,李白放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面對生與死的決擇,文天祥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漫游在這詩的國度,感受著詩香四溢,覺得自己的靈魂得到凈化,精神得到升華。
與詩交流,詩意人生,令我沉醉與向往!
有詩相伴
無論是春光乍現(xiàn),還是秋水波瀾,無論是夏花掩目,還是雪映庭院,如果生命有一日,我便讀你一天,晨,手捧朝霞伏案;午,細品陽光絢爛;夜,解讀銀河星漢。有你相伴,我便不會孤單。
有詩相伴,便有自信相伴。我可以從“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中揚起自信之帆,我可以從“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中撐起自信的長蒿,我也可以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到自信之舟,我還可以從“處士禰衡俊,諸生無縣貧”中尋到自信的支點。
篇(9)
戈麥,原名褚福軍,1967年生于黑龍江省蘿北縣寶泉嶺農(nóng)場,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9年畢業(yè)后被分配至《中國文學》雜志社工作,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萬泉河。至今日,戈麥離開人世已經(jīng)十二個年頭了,但他的詩歌仍不如比他稍早時期的北大詩人海子、駱一禾等人那樣知名。戈麥的長期被“埋沒”,并不證明他的詩歌是平庸之作,相反,這位把詩歌作為“語言的利斧”的詩人,生前一直致力于在自己的詩歌中發(fā)現(xiàn)語言突破之可能,并通過語言張力的運用使詩歌本身呈現(xiàn)出詞與詞、句與句之間的緊張感,互否與悖論充斥與詩句之中。正如同戈麥對詩歌的理解中所陳述的那樣,他的詩歌的確是“在詞與詞的交匯、融合、分解、對抗的創(chuàng)作中,一定會顯現(xiàn)出犀利奪目的語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i因此,對戈麥詩歌語言中呈現(xiàn)出來的張力進行分析,能夠從一個角度展示戈麥詩歌的美學特征,也使這位喜歡一切“不可能”的事物的詩人的作品的價值得到應有的評價。
一.詩歌語言中的“張力”概念綜述
“張力”一詞,本是物理學術語,是指事物之間與事物內(nèi)部——力的運動所造成的緊張狀態(tài)。1937年,艾倫·退特首先將張力引入詩學,主要在事物內(nèi)涵和外延的范疇上進行討論。稍后,1943年羅伯特·潘·沃倫進一步提出詩歌解構的本質(zhì)即張力的觀點,新批評流派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魯克斯最終確定了張力在詩歌藝術中的“本體性”地位。因此,“張力”是一個從西方文論中引進的概念。然而,在中國古典哲學、詩學中,“張力”的含義也隱約有所體現(xiàn),但尚未形成完整、具體的言說系統(tǒng),如道家強調(diào)的“有無相生”、格律詩中的“一字易詩”(如“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的運用)等。所以,“張力”的被提出,有其歷史淵源。
中國大陸近年來對詩歌語言中“張力”這個概念的研究,比較系統(tǒng)和具體的有陳仲義教授。本文所引用的觀點大多來自于他在2012年的著作《現(xiàn)代詩:語言張力論》一書。陳仲義教授在書中對“張力”一詞做了這樣的定義:“張力是詩語活動中局部大于整體的增值,詩語的自洽能力(即“自組織”狀態(tài))以最小的‘表面積’(容量)獲取最大化詩意。”ii并且陳仲義教授認為,詩歌語言中的“張力”是“對立因素、互否因素、異質(zhì)因素、互補因素等構成的緊張關系結構”iii,因此“張力”主要體現(xiàn)為詞與詞、句與句以及整體與部分之間通過“差”與“合”建構起來的,在語感方面給讀者緊張感、驚奇感的語言藝術修辭效果。不僅如此,詩歌語言中的“張力”還可以讓讀者更深刻地感受到詩人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思想與情感,“張力”的存在好比潛伏、流動于詩歌內(nèi)部的熾熱熔巖,使詩人的平淡語言充滿力量。因此,“張力”對詩歌語言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富有張力的詩歌語言,自然也是富有詩性的詩歌語言。“張力”的存在能彰顯一個詩人運用語言的藝術功底。
二.戈麥詩歌語言中的“張力”分析
如前文所述,“張力”對于詩歌語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戈麥,作為一名熱愛語言、重視語詞、“意識到我們時代的語言的弱點并竭力創(chuàng)造新的語言元素來加以矯正”iv的詩人,在詩歌中運用“張力”完全是潛意識中對語言的創(chuàng)新,也是個人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字功底的體現(xiàn)。不僅如此,戈麥對詩歌語言“張力”的運用也是“利用樸素的形式傳達超負荷的情感”v的需要,他在表達上追求客觀性,將內(nèi)心熾熱的情感壓縮至近乎于“無”的境界,呈現(xiàn)出一“冷”一“熱”的對比,這種對比在他自《誓言》之后的那些詩作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詩人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人類中的一員”的所有悲劇與不幸,他對人類的命運始終保持著警覺態(tài)度,并對俗世生活表現(xiàn)出了排斥。而語言讓戈麥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通過“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這種對詩歌語言“張力”的自覺追求,使戈麥“在自己和語言之間建立了一種特殊和親密的關系,他從中找到了生命的拯救”。vi因此,戈麥雖然自沉于萬泉河,使自己的肉身在塵世中消失,但他的靈魂卻在詩歌語言中得以保存,讀戈麥的詩歌,便會感受到他看似平淡、冗長、繁瑣甚至晦澀的語言背后“張力”的奔流,“張力”的存在使他的詩歌語言不同于稍早于他的海子的“熱烈”,也不同于駱一禾的“平靜”,而是類似于兩者的綜合,呈現(xiàn)出“外冷內(nèi)熱”的特點。而具體到文本,戈麥詩歌語言中的“張力”又有如下特點:
1.否定性連接詞的大量運用,如“不可能”“不是”“不會”“不好”等,使連接起來的意象和詩句之間產(chǎn)生尖銳的對立感和緊張感,通過“不可能“來達到詩人心目中的“可能性”。如《界限》:“發(fā)現(xiàn)我的,是一本書;是不可能的。/飛是不可能的。/居住在一家核桃的內(nèi)部,是不可能的。/三根弦的吉他是不可能的。/讓田野裝滿痛苦,是不可能的。/雙倍的激情是不可能的。/忘卻詞匯,是不可能的。/留,是不可能的。/和上帝一起消夜,是不可能的。/死是不可能的。”詩人先設置了一系列陳述句和意象,然后立即進行斬釘截鐵的否定:“……是不可能的。”那什么是“可能性”呢?詩人并沒有直接回答。但細讀詩篇,結合詩人生平的信念和觀念,可以推測出詩人雖然對現(xiàn)實生活和人生命運持悲觀態(tài)度,但詩歌使他發(fā)現(xiàn)了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他把自己的靈魂置于詩句中,因此“死是不可能的”。戈麥詩歌中運用否定性連接詞的例子還有“學不會的舞蹈”(《命運》)“不再理會活的東西”(《我要頂住世人的咒罵》)“生活是再也編織不好的花籃”(《我是一根剔凈的骨頭》),等等。詩人對現(xiàn)實中的“存在”總體上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現(xiàn)實不過是一場令人驚悸的破碎的噩夢”,因此他“渴望一種超越的生活”“向往現(xiàn)實背后的彼岸世界”vii,所以戈麥在詩歌中設置的否定,實質(zhì)上是為了達到心中對“超越”、對“彼岸”的肯定,在“否定——肯定”之間,張力得到了凸顯。
2.戈麥對于富有“絕對性意味”的詞語的喜愛,在他的詩歌語言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戈麥喜歡把話說“絕”,與前文所述的否定性連接詞的運用一起促成了詩歌中的緊張感,并彰顯出詩人在詩句中流露出來的對世界、對人類徹頭徹尾的絕望。如“人類呵,我要徹底站在你的反面”(《我要頂住詩人的咒罵》)“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竟能夢見/這荒蕪的大地,最后一粒種子/這下垂的的時間,最后一個聲音/這個世界,最后的一件事情,黃昏的星”(《獻給黃昏的星》),同時,戈麥詩歌中的“絕對性”詞語的運用也有“完成性”的意義,就像海德格爾所說,“只要此在存在,它也向來已是它的尚未”viii。而“最后”“毀滅”“死亡”這些詞語,在意味著“存在”的終結的同時,也意味著它的完成:“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ix。如詩人在《誓言》中所述:“好了。我現(xiàn)在接受全部的失敗/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著小眼兒的雞蛋/好了。我已經(jīng)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僅僅一次,就可以干得異常完美。”戈麥的生前好友西渡認為,《誓言》這首詩標志著戈麥的寫作風格從此發(fā)生了重要轉(zhuǎn)折,詩人從而更為徹底、決絕地拒絕俗世生活,走上一條追求內(nèi)心理想完整性的道路,直至死亡。
3.戈麥詩歌語言中的“張力”還有一個表現(xiàn)是戈麥善于把表面上相互之間沒有關聯(lián)的詞語用“串珠串”的方式連接起來,把它們組合成詩句。這使戈麥的詩歌語言簡短、簡潔、富有力度的同時,又增加了讀者理解戈麥詩歌語言的難度,有時甚至晦澀。這些詩歌多以“十四行詩”的面目出現(xiàn),也從一個角度說明戈麥對于詩歌語言形式規(guī)范的嚴謹性。如《愛情十四行》《兒童十四行》《歡樂十四行》等。《愛情十四行》的主題是“愛情”,但詩句中出現(xiàn)的卻是與“愛情”不相關的詞語:“黑夜。苦水。照耀中的日子。/早晨的花。一個瞎子眼中的光明。/蒼白的腳趾。苔蘚。五行血的歌子。/死者喉中翻滾的話語。/不知名的犧牲者。殘廢的啞巴。……”一個詞,就是一句詩,運用了一種類似于“換喻”的手法。所謂“換喻”,“是以密切相關的事物在推理過程中從本來事物轉(zhuǎn)換到另一事物去”x,因此詩中出現(xiàn)的詞語,表面上看與“愛情”沒有太大聯(lián)系,給讀者一種陌生感,這是因為詩人常對“此在”的人生存在懷疑與悲觀情緒,“愛情”在詩人眼中也是具有消極意義的,而詩歌中出現(xiàn)的詞語,如“黑夜”“苦水”“死者喉中翻滾的話語”等,皆有悲傷、痛苦、短暫的特點,無形中契合了詩人心中對“愛情”主題的認知,把個人的情感緊密在包裹在詞語的內(nèi)部,如果不仔細品味,很難發(fā)現(xiàn)詩中所指,也很難體會詩人的感情。因此戈麥的詩歌語言,有一種“謎語”的韻味,這便是“張力”造成的效果。
4.戈麥詩歌語言中出現(xiàn)的色彩,也呈現(xiàn)出視覺上的“張力”感,這是因為戈麥把色彩的傳統(tǒng)象征意義取消了,換之以陌生的意義,用來表達詩人的獨特認知,與整首詩的氛圍相契合。縱觀戈麥的詩歌,這種“陌生化”效果最顯著的是對“綠”的運用。有的研究者曾認為戈麥對“綠”是持一種“厭棄的態(tài)度”xi,其實細察戈麥詩歌中出現(xiàn)“綠”的詩句,其中蘊含的情感的不僅是“厭棄”,還有“絕望”“悲傷”的寓意,給人一種冷冽的感覺,甚至與死亡相掛鉤,與“綠”在傳統(tǒng)意義中所持有的“生機、美麗、活潑”等具有積極意味的意義相逆反。如“死死命定的冰冷/指甲已染為綠色”(《經(jīng)歷》)“那些冷綠的太陽/從不曾預期的位置/向你走來”(《冬天的對話》)“在云渦中抖動的是一顆發(fā)綠的心/在一朵黑云上張望的是一個靈魂的空殼”(《大風》)等。這種對色彩陌生化意義的運用,與海子在后期詩歌中對“桃花”色彩的描寫有相似之處。人們經(jīng)驗中的桃花是粉紅色的,從色彩學上講,這是一種柔和的,給人以美好希望的色彩。而海子筆下的桃花卻是血紅色的,這是一種處于壓力與爆炸力邊緣的顏色,從某種程度上講,血紅比黑色更黑暗xii。海子對桃花的色彩進行了“變形”,而戈麥也對自己詩歌中“綠”的色彩意義進行了變形,“張力”即在“變形”中產(chǎn)生。
“語言對個人的壓力常常轉(zhuǎn)而表現(xiàn)為個人對語言的貪婪。”xiii正如臧棣所說,對語言的珍愛以及對語言“張力”的運用造就了戈麥詩歌的“尖銳”的特點,這在當代詩歌史上是一個較為獨特的現(xiàn)象。但對語言的熱烈追求,也使得戈麥的詩歌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加速”的特點,加之戈麥自覺地“站在人類的反面”,因此他的詩歌在冰山般的表面下是洶涌奔突的火海。戈麥在詩歌語言中找到了通向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但他卻使自己的肉身消遁于塵世中,只留下他的那些閃爍著苦痛靈魂的詩作,以及他的格言:“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1.戈麥:《戈麥詩全編》,西渡編,上海文聯(lián)出版社,1999年。
2.陳仲義:《現(xiàn)代詩:語言張力論》,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
3.譚五昌:《詩意的放逐與重建》,昆侖出版社,2013年。
4.孫基林:《崛起與喧囂——從朦朧詩到第三代》,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
5.【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
6.孫佃鑫:《戈麥詩歌色彩論》,《劍南文學(經(jīng)典教苑)》,2012年第5期。
7.吳 昊:《海子詩歌中的桃花意象分析》,《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注 釋:
i戈麥在《關于詩歌》一文中曾有如下觀點:“詩歌直接從屬于幻想,它能夠拓展心靈與生存的空間,能夠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原載《詩歌報》1991年第六期。
ii 陳仲義:《現(xiàn)代詩:語言張力論》,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88頁
iii 同上,第73頁
iv 臧棣:《犀利的漢語之光——論戈麥及其詩歌精神》,《戈麥詩全編》,西渡編,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438頁。
v 譚五昌:《詩意的放逐與重建》,昆侖出版社,2013年,第252 頁
vi 西渡:《拯救的詩歌和詩歌的拯救》,《戈麥詩全編》,西渡編,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454頁。
vii 孫基林:《崛起與喧囂——從朦朧詩到第三代》,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第127頁。
viii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 282頁。
ix 同上,第302 頁。
x陳仲義:《現(xiàn)代詩:語言張力論》,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28頁。
xi 孫佃鑫:《戈麥詩歌色彩論》,《劍南文學(經(jīng)典教苑)》,2012年第5期。
篇(10)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雖然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歷程,但是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浪潮中,卻涌現(xiàn)了一大批新文學作家,開啟了文學現(xiàn)代性的新紀元。一大批新詩人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如冰心、宗白華、馮至等,而馮至作為現(xiàn)代詩歌的一員大將,魯迅先生在回顧20年代新文學時,稱他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而經(jīng)過時間的檢驗,也證明了馮至的詩是經(jīng)得起歷史的挑剔的。這其中又以他的《十四行集》最為著名,而馮至是從里爾克的變體詩中得到了啟發(fā),開始了十四行詩的創(chuàng)作,并且將這種詩體和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結合起來,對詩的雕塑美、對個體存在的孤獨性、對死亡哲學的理解等都進行了深層次的探詢。
一、馮至對十四行詩體的吸收和創(chuàng)新
(一)對十四行詩的嘗試性創(chuàng)作
隨著西方文學的涌入,十四行詩這一新的詩歌體式也被介紹到了中國,馮至受到里爾克變體十四行詩的啟發(fā),開始進行十四行詩的創(chuàng)作。當他在觀察自然萬物花鳥魚獸時,在體悟整個世界的紛繁無序的世事時,詩歌開始在他胸中自然的流淌。這同里爾克所秉持的觀點基本一致,在他看來,只要是這個世界真實存在的,就沒有不可以入詩的,他在《布里格隨筆》里寫到“等到它們成為我們身內(nèi)的血、我們的目光和姿態(tài),無名地和我們自己再也不能區(qū)分,那才能以實現(xiàn),在一個很稀有的時刻有一行詩的第一個字在它們的中心形成,脫穎而出”[2],而馮至的十四行詩正是從那狂風乍起的中心形成,在那秋風里蕭蕭的玉樹間脫穎而出。
在進行十四行詩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馮至從里爾克那里學會了觀看,學會了發(fā)現(xiàn)事物的魂靈。如他在《十四行集》的第二首里寫的那樣“把樹葉和些過遲的花朵/都交給秋風,好舒開樹身/深入嚴冬;我們安排我們/在自然里,像蛻化的蟬蛾/把殘殼都丟在泥里土里”[3]在這里,馮至通過對樹、花、蟬蛾、殘殼等自然物的觀看,將這些事物的魂靈解析出來,并且給予哲理上的思考,認為在無限的世界中,必然死亡的生命歷程就像蟬蛻一樣沒入塵土,所有的一切可以歌唱的都被默默的青山消解,而人的存在本質(zhì)也在這種消解中被隱喻。
(二)對舊十四行詩的掙扎和創(chuàng)新
馮至的詩歌創(chuàng)作吸收了里爾克的變體十四行詩的創(chuàng)作形式,而且也不拘泥于詩歌的十四行韻和嚴格的對仗體式,同時也加入了很多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群,如其《二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二首“深夜又是深山/聽著夜雨沉沉/十里外的山村/念里外的市廛/它們可還存在?......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在這首詩里詩人創(chuàng)造了深夜、深山、夜雨、山村、市廛等一系列物象,形成一種古樸、沉厚的意向群體,而詩的最后兩句更是整首詩的點睛之筆,將作者內(nèi)心對擺脫束縛、走出自我困境的渴求,這首詩將現(xiàn)在主義哲學和古典主義意象進行了完美的結合。
里爾克在他的詩《預感》中說“我像一面旗被包圍在遼闊的空間......我認出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我舒展開又跌回我自己”。里爾克在這里將自己物化為孤獨的旗幟,在表達在風暴中獨自起落時的自我忍耐具有救贖的神性和自我的成全,這種物我合一的哲理性詩句也正是馮至在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所追求的一種詩意,但是他的詩意更具有中國古典氣息,如他在《從一片泛濫無形的水里》結尾所寫的那樣“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這首詩可以說是馮至《十四行集》的創(chuàng)作宣言,既包括了詩人的一種感性的詩意抒發(fā),又包括了對萬物存在的一種理性思考和哲學意味,@種理性的哲思正是馮至對里爾克的吸收和繼承。
二、馮至對里爾克經(jīng)驗詩學的吸收和掙扎
(一)詩是經(jīng)驗
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認為“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4],但是里爾克卻認為人類本身就具有情感性,而我們更需要的是經(jīng)驗。里爾克對馮至的影響就在于將馮至從浪漫主義抒情性帶入到經(jīng)驗詩學。我們通過馮至的很多詩歌可以看到作者對于詩歌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如詩人早期的詩《夜步》寫寂寞,是“我永久從這夜色中/拾來些空虛的惆悵!”,而在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詩人的寂寞就化作了一脈的青山默默。詩人摒棄了原先那種“全身血液沸騰”的寫作,而主張以一種嚴謹性的閱讀積累和認真觀看來對自然宇宙進行經(jīng)驗化的哲理抒寫。
里爾克的創(chuàng)作也是一種逐漸經(jīng)驗化的過程,他也有過“情感泛濫”的時候,如他寫愛情的瘋狂“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見你”。而在他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這種情感的外露則演變成了一種謙遜的經(jīng)驗化寫作,他更注重外物的本原對自我內(nèi)心的映照。而馮至正是吸收了他這種寫作方式,擺脫了之前的寫作困境。如從他30年作的《威尼斯》“傍晚穿過長怨橋下,只依稀/聽見了嘆息三兩聲”,到他40年代的《十四行集》的第五首“一個寂寞是一座島/一座座都結成朋友”,雖然是對同一座城市的回憶,所要表達的依舊是關于寂寞的主題,但是后者卻更為嚴謹,情感也更為克制,也更具有經(jīng)驗化的詩學特征。
(二)馮至詩的古典性和歌德情懷
馮至的詩歌不僅具有現(xiàn)代主義、古典主義特征,同時也受到了歌德的影響。馮至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將中國傳統(tǒng)的古典詩藝和西方的韻律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十四行詩,如他的《十四行集》中的第二十一首“銅爐在向往深山的礦苗/瓷壺在向往江邊的陶泥/他們都像風雨中的飛鳥/各自東西”里運用了許多具有中國古典特色的意象,如“銅爐、瓷壺、飛鳥”等,也與中國古詩中借景抒情的特點一脈相承,小小的茅屋、吹起一切的狂風和又將一切淋入泥土的暴雨,這一切場景的組成也可以看作對杜甫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再創(chuàng)作。在這里詩人又巧妙地運用西方新的思維模式和句子結構,寫銅爐向往礦苗、瓷壺向往陶泥,將物人格化,句子別致巧妙,具有現(xiàn)代主義特征。
如果說馮至與里爾克的相遇是一種宿命,那么馮至的歌德情懷則是一種必然。他的《十四行集》中的第十三首就是關于歌德的一首詩,他在這首詩的寫道:“你知道飛蛾為什么投向火焰/蛇為什么脫去舊皮才能生長/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與變”,馮至在這里直接化用了歌德《幸福的渴望》里的詩句“飛蛾,你追求著光明/最后在火焰里獻身/只要你還不曾有過/這個經(jīng)驗:死和變!”,在這個時期馮至雖然走出了情感泛濫式的寫作,但是其精神困境仍然存在,里爾克的謙遜和忍耐也不足以為馮至提供一個出路,而歌德的生存智慧和人生經(jīng)驗就吸引了馮至的注意,這個時候的馮至無論是在自我精神方面還是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都渴望實現(xiàn)一場新的“死與變”,而這種死與變是克制的,更是具有生命力的。
三、馮至關于孤獨的哲學思考
(一)宇宙中的一個人
從馮至發(fā)表他的第一首詩歌《綠衣人》開始,孤獨就一直是他詩歌揮之不去的情感表達,這種孤寂悲傷的感情基調(diào)和詩人童年母親的去世有關的,而這同里爾克早年感受到被母親驅(qū)逐的恐懼和脆弱的感情是相通的。里爾克在他的《嚴重的時刻》中寫道“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在世上哭/在哭我”,在這首詩里,詩人將自我的感受擴大化為人類共同的命運,詩中“某處”“無緣無故”將人類在命運面前的那種孤獨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寫的極為深刻。而馮至在其《十四行集》第六首中寫哭泣的農(nóng)婦和村童,“我覺得他們好像從古來/就一任眼淚不住的流/為了一個絕望的宇宙”,這種脆弱莫名的哭泣其實和里爾克《嚴重的時刻》中無緣無故的哭泣是一樣的,面對浩瀚的宇宙,人的渺小和事世的無常都將人推入到一種孤獨的絕望之地,只是馮至寫得更為脆弱具體。
對馮至而言,里爾克存在就像他人生的一面鏡子,映照出其生命中孤獨的時刻,并且?guī)ьI他走出情感的荒蕪之地。在馮至看來:“在人間有像里爾克這樣偉大而美的靈魂,我只感到海一樣的寂寞,不再感到沙漠一樣的荒涼了”。最初,馮至的寂寞是一條蛇,冷冷的沒有言語,后來馮至的寂寞是一塊磨刀石,逐漸磨掉了他心中情感的枝枝蔓蔓。他在《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二首中寫道:“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詩人在面對遙遠的山川和久遠的幻夢時,個人的孤獨猶如在母胎里的孤獨,而我們狹窄的心所渴求的不過是一個的宇宙,而這個宇宙卻是孤獨的,就像永遠低頭行走的G衣人,可怕的時辰到了!
(二)一個人的宇宙
對于馮至而言,里爾克教會了他發(fā)現(xiàn)宇宙萬物本身的姿態(tài),并分擔他們孤獨的命運,這也正是馮至從宇宙中的一個人走到一個人擁有一個宇宙的重要的一步。在他看來,人的生命本身存在是與宇宙萬物是融為一體的,我們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都與我們有著莫大的聯(lián)系。他在《十四行集》的第十六首中寫到:“哪條路,哪道水,沒有關連/哪陣風,哪片云,沒有呼應/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在這里詩人將自我融入到整個宇宙中來,化成了平原、蹊徑,與每一道水、每一陣風相呼應,所有經(jīng)過的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從這種意義上說,人并不是在孤獨中等待死去,而是在孤獨中與世界達成統(tǒng)一。
里爾克在他的秋日里寫道:“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在他的詩歌里,孤獨的底色仿佛是一個巨大的幕布,籠罩一切,而馮至就是在這種幕布下小心翼翼的行走,努力尋找自我靈魂的出口。他在《一個消逝了的村莊》中所塑造的那個坐在夕陽之下山丘之上,聚精會神的縫著什么東西的村女形象其實就是詩人寧靜的內(nèi)心世界的一個鏡像,她讓詩人知道了“一個小生命是怎樣鄙棄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擔當者一個大宇宙”。而這也正是馮至走過里爾克孤獨幕布后內(nèi)心達成了自我的和解。
馮至曾經(jīng)說過:“我不迷信,我卻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學方面存在著一種因緣。”對于馮至而言,這種因緣或許就是指的就是同里爾克的相遇。德國抒情詩人荷爾德林有一句詩“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馮至與里爾克的相遇,則是這種詩意棲息的必然,里爾克就如同那風中孤獨的旗幟,指引著馮至走向詩意的棲息之地。在這詩意的棲息之地,馮至不僅走出了那個“沒有花,沒有光,沒有愛”的胡同,而且進入了一個真實的、沒有夸耀的春天。
注釋:
①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第5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
②賴納?馬利亞?里爾克.《里爾克讀本》馮至、綠原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③馮至《馮至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④威廉?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序言》
參考文獻:
篇(11)
古典詩歌經(jīng)過兩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變過程。新詩擁有舉世矚目的古典詩歌的雄厚基礎,本當可以取得比較滿意的生長周期,但新詩由于在與舊詩的決裂中誕生,帶有“先天貧血”,加之歷經(jīng)困擾,因而延緩了本世紀新詩的發(fā)展過程。然而作為一種新生詩體,又總是以潛在的生命力,尋找一切復蘇和健全自身的機遇。伴隨著每一次對新詩的重新認知和藝術建設,都有利于新詩向現(xiàn)代漢語詩歌方面的藝術轉(zhuǎn)變。
本文運用“漢語詩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來中國新詩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追尋新詩的漢語言藝術的本性。
一、“新詩”的猝然實現(xiàn):中國詩歌的自由精神的張揚與漢語詩意的流失
19世紀西方科學文化的迅速興起,構成對中國古老文化的嚴峻挑戰(zhàn),“詩國”便漸漸有了閉關自守的頑固堡壘的意味。中國詩壇的先覺們走出國門,睜開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對“詩國”的反省,“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然而能否在漢語詩歌的基礎上實行變革?則成了20世紀詩壇的焦點。“詩界革命”雖未促成新詩的誕生,但梁啟超、黃遵憲等并不割斷與詩國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論詩,還是可取的。新詩作為“五四”詩體解放的產(chǎn)兒,是背叛傳統(tǒng)漢語詩歌的“逆子”。“五四”先驅(qū)出于要改變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詩國”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簡單化的方式。所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表明了這種“革命”———“推倒”的決心。他們疏忽了一個事實:古代詩歌的格律化與白話化,幾乎在同步演變。至唐代產(chǎn)生的格律詩又稱近體詩、今體詩,從“白話”的角度理解這一命名,似乎更為貼切。即使“古體”,也發(fā)生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石壕吏》、岑參的《白雪歌》等,可視為半“自由”、半白話詩。唐詩宋詞得以在民間留傳,乃至成為今日兒童背誦的啟蒙課本,豈不正是其白話格律或白話古體的原因?“五四”變革者對白話或半白話的近體詩與文言散文及其他韻文不加區(qū)別,打破“格律”,同時也將充滿詩意的白話口語的煉字、煉句、語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這種在“短時期內(nèi)猝然實現(xiàn)”的新詩,使凝聚了中國人幾千年審美感知的詩性語言在一夜之間流失殆盡。“五四”先驅(qū)們讓對“詩國”的叛逆情緒,掩蓋了對古典詩歌藝術價值的認識,他們以驚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沒有注意到國門打開之后,中國幾千年的詩歌庫藏同樣對西方產(chǎn)生著新異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國現(xiàn)代意象派詩人龐德十分推崇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神韻,譯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創(chuàng)造了漢語詩歌的新奇動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幾乎在一張白紙上誕生了新詩,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學步的幼稚狀態(tài)。“詩該怎樣做”呢?自己也說不清楚。所謂“變得很自由的新詩”,“有甚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①,雖在提倡很自由地說真話,寫口語,卻沒有劃清詩與文的界限。提出關于新詩體節(jié)的“自然節(jié)奏”、“自然和諧”②,也因?qū)挿憾y以作詩的把握,當時詩壇處于茫然無措之中。有趣的是,變革家們雖然執(zhí)意要“推倒”舊詩,但寫起詩來卻“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脫不了古體詞曲的痕跡。只是光顧得模仿古典詩詞的意味音節(jié)去保持“詩樣”,卻忽視和丟掉了詩意空間建構的方式,致使專說大白話,詩味匱乏。俞平伯試驗用舊詩的境界表現(xiàn)新意。他曾作切膚之談:“白話詩的難處,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詩上面”,“白話詩與白話的分別,骨子里是有的”③。劉半農(nóng)得力于語言學家的修養(yǎng),他駕御口語的能力、大膽的歌謠體嘗試、及其“重造新韻”、“增加無韻詩”、“增多詩體”等主張④,對于草創(chuàng)期詩歌的轉(zhuǎn)型、特別是新詩體建設,具有倡導性意義。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蕪中矗立起新詩的旗幟,難免顯得創(chuàng)造力的貧乏,便不得不從西方詩歌中汲取靈感。伴隨20年代始,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出現(xiàn)在詩壇,意味著新詩的長進。與其說是從西方闖入的“女神”,不如說是“五四”時代呼喚的“女神”。郭沫若從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中汲取了詩情,在感應和效法美國詩人惠特曼那種擺脫一切舊套的博大詩風中,把自由體連同西方現(xiàn)代詩歌慣用的隱喻和象征的詩意方式一起引進來了。這就增強了自由的新詩的形式內(nèi)涵,彌補了草創(chuàng)期新詩的不足,具備唱出“五四”時代最強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個人的郁結民族的郁結,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⑤。那種“天狗”式的絕唱,“鳳凰涅*$”似的再生,“爐中煤”燃燒般的感情……一個個形象感人的博大隱喻,凸現(xiàn)著思想解放和“人的覺醒”的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郭沫若可稱為“中國的雪萊”,“是自然的寵子,泛神論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⑥,將詩視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詩人任其情感隨意遣發(fā),無拘無束,讓自由精神之馬沖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詩的疆界,導致詩體語言的失范、粗糙,散漫無紀。郭沫若對“美人”的比喻,不盡妥貼。因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體美的展示,而“不采詩形”,豈不喪失了詩美傳達的媒體?
新詩自由體的匆匆登場,決定了漢語詩歌的命運。可以說,“五四”“詩體解放”并不屬于自覺的文體革命。但“詩國革命”作為“五四”的突破口,卻實現(xiàn)了文學思想的解放和轉(zhuǎn)變。先驅(qū)們致力于使詩和文學從森嚴壁壘、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識王國里突圍,回到人性復蘇、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現(xiàn)代精神家園中來。“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舊了的衣囊/我為容受你們的新熱、新光,/要去創(chuàng)造個新鮮的太陽!”(《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對新詩的貢獻,不在于引進自由體,而在為高揚新詩的自由精神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隱喻的詩意方式,這個“新鮮的太陽”,揭開了20世紀詩歌的黎明的天空,使?jié)h語詩歌進入了現(xiàn)代精神的家園。
作為舶來品的“自由體”,如何植根于中國詩苑?回答很簡單:要契入中國詩體藝術,成為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自由體。郭沫若的大多數(shù)自由體詩是激發(fā)型的,伴隨“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漢語詩性語言那種不可磨滅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顯重視了漢語詩歌的音節(jié)和“外在的韻律”,甚至趨向半格律體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天上的市街》、愛情詩集《瓶》中的《鶯之歌》等具有漢語特色的作品。但后來多數(shù)篇什已經(jīng)意味著他的詩力不足而失去了藝術探索的能力。
舊詩體在“五四”詩體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個人化寫作的性質(zhì)。郁達夫一方面肯定和稱贊新詩“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對“詩國”的眷戀,表現(xiàn)了運用舊詩體創(chuàng)作的興趣和才情。他和形成與郭沫若之間新舊體詩互比互補的“創(chuàng)造”景觀。這一典型個案,構成了第一次漢語詩歌轉(zhuǎn)變的窘迫情境。
二、從“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漢語詩歌藝術轉(zhuǎn)變的契機
任何民族的新舊語言文化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新詩與母體的隔膜是暫時的,終究要返回對母體的追認,不過歷經(jīng)了一個浪跡天涯的過程。
中國新詩的“貧血癥”,以西法治療滋補,盡管不能“治本”,但也會“活血強身”,拓寬視野。中國自文學革新后,詩界百無禁忌,是詩人敢于試驗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國門與留在國內(nèi)的詩界有識之士,紛紛向西方現(xiàn)代派詩歌尋找新詩的出路,20年代中國新詩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態(tài)勢。尤其是象征主義詩歌藝術那種富有內(nèi)含力和迷離色彩的詩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詩的靈驗秘方。這一時期新詩明顯向內(nèi)在、含蓄、渾沌方面轉(zhuǎn)變,雖未很快轉(zhuǎn)化為漢語詩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種模仿或復制,然而,新詩即使充當西方現(xiàn)代詩歌的“拿來文本”,也會給漢語詩歌帶來新異感,進而反觀自身,達到對異質(zhì)語言藝術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現(xiàn)代漢語詩歌文本。
一位優(yōu)秀詩人不管接受多少外來詩歌藝術的影響,都離不開深厚的民族語言文化和詩歌傳統(tǒng)藝術的支撐。20年代中后期中國詩人從“打開國門看世界”進入“從世界回首故國”。創(chuàng)造社穆木天的《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與稍后周作人的《<揚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頗能表明這一歷史性轉(zhuǎn)折,也可以理解為新詩開始對母語的追認。穆木天留學日本,從熟讀法國象征派詩歌和英國唯美派王爾德的作品開始新詩創(chuàng)作,但他沒有一味陶醉于“異國熏香”,而是審視和反思新詩自身,主張“民族彩色”。他認為“中國人現(xiàn)在作詩,非常粗糙”,批評“是最大的罪人”,“作詩如作文”的主張是“大錯”。周作人明確提出建立新詩與漢語詩歌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詞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擺脫不掉的”,并認為漢語詩歌的字詞組合及修辭方法具有超越時間的延續(xù)性。即是被認為“歐化”的詩人李金發(fā),也批評文學革命后“中國古代詩人之作品”“無人過問”的傾向,主張在創(chuàng)作中對東西方的好東西進行“溝通”和“調(diào)和”,而體現(xiàn)在他的詩作中只是歐化句法與文言遣詞兼而有之⑩。穆木天從對“詩國”藝術的勘探中,提出“純粹詩歌”的要義有四:(一)要求詩與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詩不是說明,而是表現(xiàn);(三)詩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詩要兼造型與音樂之美。這顯然是對的新詩理論的反撥。如果說穆木天的“純粹詩歌”已找到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契合點,那么周作人特別強調(diào)的“融化”概念,則是實施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內(nèi)在機制。他認為“把中國文學固有的特質(zhì)因了外來影響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詩本來也是從模仿來的,它的進化在于模仿與獨創(chuàng)之消長,近來中國的詩似乎有漸近于獨創(chuàng)的模樣,這就是我所謂的融化。”“融化”,是實現(xiàn)漢語詩歌的藝術轉(zhuǎn)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新詩由于發(fā)生了詩歌語言傳統(tǒng)之力與現(xiàn)代詩歌藝術方式的雙重危機,因而“融化”意味著新詩向民族化、現(xiàn)代化的雙向轉(zhuǎn)化。新詩從“模仿”到“獨創(chuàng)”的實現(xiàn),是一個尋根和創(chuàng)新的過程。一方面從“詩國”中汲取母乳,恢復和增強漢語詩歌的固有特質(zhì),一方面使“拿來”的西方現(xiàn)代派詩歌藝術真正為漢語詩歌藝術所汲收和消化。新詩徹底擺脫“模仿”的印記,表現(xiàn)為回歸母語的自我消解。“獨創(chuàng)的模樣”,固然要使?jié)h語詩歌的特長和優(yōu)勢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視著世界詩歌潮流的藝術折光。“融化”發(fā)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詩藝的相通之處。譬如,19世紀末西方開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稱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詩”。周作人認為“象征實在是其精意。這是外國的新潮流,同時也是中國的舊手法;新詩如往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國新詩也就可以產(chǎn)生出來了”。“真正的中國新詩”正是以復蘇漢語的本性與孕發(fā)更多的詩意為目的,與以前的“新詩”劃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詩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確的現(xiàn)代漢詩意識,即使突入“融化”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也并不意味有了實現(xiàn)漢詩轉(zhuǎn)變的藝術自覺。我們只能從各路詩家勇于求索、自由發(fā)展的撲朔迷離的態(tài)勢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詩向現(xiàn)代漢語詩歌方面轉(zhuǎn)化和發(fā)展的軌跡。
一種是從詩形切入,試驗作漢語形式的新詩。1926年4月新月社聞一多、徐志摩等創(chuàng)辦《晨報·詩鐫》,提倡“詩的格律”,無疑是對初期新詩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詩形式重建的氛圍。然而聞一多所說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譯意,具體指“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jié)的勻稱,有句的均齊”,“聽覺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韻腳”瑏瑡。中外詩歌在視、聽覺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處,但漢語方塊字有著自身獨有的組織結構和美學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詩的視覺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現(xiàn)了與字母文字不同的語境方式和操作程序。聞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論者和教科書中所說是“中國古詩傳統(tǒng)與外來詩歌形式的結合”。考察當時在《詩鐫》、《詩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節(jié)的“豆腐干塊詩”,包括被認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難說體現(xiàn)漢語詩歌的“格律”,更談不上與漢字詞匯的詩意方式融于一體。光圖有詞句的整齊排列,而缺乏煉字煉句煉意的工夫,就建構不起漢語詩歌意義生成系統(tǒng)的優(yōu)化結構和詩意空間。這種不能發(fā)揮聽、視覺方面的漢語詩歌特長的“格律”,難免有西洋“格律”的漢譯化之嫌。朱自清評論“他們要創(chuàng)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瑏瑢。當然,他們有些作品,如聞一多的《一句話》、《收回》,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偶然》、《沙揚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較切入現(xiàn)代漢語的音樂節(jié)奏,自然流暢,在整飭中求變化,避免了因?qū)ψ衷~的相等對應的刻意追求而出現(xiàn)的滯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試驗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著現(xiàn)代漢詩的特色。這位對西方詩體和詩律學研究頗深的詩人,具有鮮明的民族語言意識,自覺發(fā)掘古典詞曲和民歌的形式結構的美。如《采蓮曲》,即是從六朝駢散和江南民歌中脫出來的。《搖籃曲》、《催妝曲》、《春風》、《月游》等,是將英國近代格律體、歌謠體與我國民歌民謠相融合而創(chuàng)造出的歌謠體,音節(jié)流轉(zhuǎn)起伏,韻律回蕩優(yōu)美,并構成整體勻稱的方塊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漢語詩意空間?仍處于探索之中。如果說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創(chuàng)造了人類自由性靈所依戀的“康橋世界”這一意味彌深的音樂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墳墓》、《廢園》等篇什,則在對某種情緒和靈魂的深度顯示中造成了較大張力的詩意場。這對于漢詩傳統(tǒng)形式的開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新月派作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客觀上溝通了詩人對新詩漢語藝術形式的重視,影響了一代人的創(chuàng)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詩、九行詩、對詩行、節(jié)奏和口語化的追求,也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漢語特點,有人稱為“現(xiàn)代絕句”。
十四行詩(Sonnet),作為從西方引進的特殊的格律體,為不少詩人所喜歡、試驗著寫過。但真正能夠切入現(xiàn)代漢語的音節(jié)和詩意的方式、試驗出色者,當數(shù)早年加盟沉鐘社的馮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嚴格遵守十四行的傳統(tǒng)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體結構上的特點,適當融入古典漢語詩詞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現(xiàn)代漢語的音節(jié)和語調(diào)的自然,體現(xiàn)了濃郁婉轉(zhuǎn)的東方抒情風格。在詩意表達上,雖明顯受里爾克的影響,卻完全從自身的藝術體驗出發(fā),以精妙含蓄的漢語,抒寫內(nèi)心真實。馮至的十四行詩,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詩歌語言之間的轉(zhuǎn)化,是對西方十四行的一種變奏體。
再一種是從詩意結構切入,運作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象征藝術表現(xiàn)。象征詩派與新月詩派大體上是平行發(fā)展的。從李金發(fā)最早以“詩怪”出現(xiàn)在詩壇,到戴望舒被稱為中國的“雨巷詩人”,表明象征派詩的演變,以漢語詩意質(zhì)素的增長為標志。李金發(fā)的詩,既是異端,又是墊腳石。“異端”相對于傳統(tǒng)而言,帶有“革命性”意味。李金發(fā)詩的深層的內(nèi)心體驗的個人象征意象,以幾分生澀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渾沌感深度感,顯示了突破傳統(tǒng)象征、給個體生命內(nèi)涵賦形的可能。然而這與現(xiàn)代漢語詩歌還相距甚遠,僅是漢語詩歌轉(zhuǎn)化中的特有場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這一場景中推動了象征派詩的漢語化進程。他們不是照搬波德萊爾、魏爾倫、葉芝、里爾克這些象征派、現(xiàn)代派大師,而是著眼于尋找西方詩與漢語詩的藝術契合點,“做‘化古與化歐’結合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認為戴望舒開始寫詩,“是對徐志摩、聞一多等詩風的一種反響。他這種詩,傾向于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將法國早期象征派詩人魏爾倫追求語言的音樂性、意象的朦朧性與我國晚唐的婉約詞風相融合,使“中國舊詩風”發(fā)生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雨巷》的現(xiàn)代漢語意味,不僅表現(xiàn)在“雨巷”這一富有民族情結和充滿漢語詩意的象征體的朦朧美,還突出體現(xiàn)了以詩人情緒為內(nèi)在結構的現(xiàn)代漢語音節(jié)的韻律美,葉圣陶稱贊《雨巷》“替新詩的音節(jié)開了一個新的紀元”瑏瑤。詩人注重漢語音節(jié),并不影響內(nèi)心開拓及詩意發(fā)掘,因為音節(jié)安排服從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詩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將中國古典詩歌的含蓄與西方象征主義詩歌語言的親切和暗示、中國傳統(tǒng)的意境與西方的“戲劇性處境”、“戲擬”相溝通和融合,形成了漢語詩歌的獨特而富有表現(xiàn)力的現(xiàn)代口語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韻節(jié)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層象征蘊涵的詩境建構方式。詩的口語化敘述方式的戲劇化、非個人化傾向,決定了詩中的“我”、“你”、“他”(“她”)互換的特點,有利于達成曲徑通幽的詩意傳達和多方位、多層次的詩意結構空間。這即是卞之琳詩歌的現(xiàn)代漢語的智性結構和深邃的哲學境界。
象征派詩歌藝術對于豐富新詩的藝術表現(xiàn)力,拓深意境,實現(xiàn)漢語詩歌的現(xiàn)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藝術實踐意義。在后來民族救亡和長期戰(zhàn)爭的背景下,多數(shù)詩人轉(zhuǎn)向愛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馬》、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優(yōu)秀詩篇,仍以象征性而顯示出不同凡響的藝術力量。
對新詩的現(xiàn)代漢語形式的創(chuàng)造和探索,未能成為后來詩人們的自覺。甚至戴望舒后來受法國后期象征派詩的影響,也在追求詩的情緒自由表達和口語化中,失去了漢語音律的節(jié)制和用語凝煉。30年代后期有論者明確提出:“假如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是詩;假如不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不是詩。”“口語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詩”,因而提倡“詩的散文美”瑏瑥。這實質(zhì)上是郭沫若自由體詩風的延續(xù)。當時蕭三、李廣田等曾對新詩形式的歐化傾向、“散文化風氣”提出過批評,但對新詩的“完美的形式”的具體建構也說不清楚。40年代在“詩歌大眾化”的理論下,民歌體詩盛行,由于詩人的感情定勢、缺乏漢語意象營造的深層結構而流于詩意膚淺。
三、五六十年代海峽一隅風景看好漢語詩歌轉(zhuǎn)變的延續(xù)
當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籠罩詩壇,大陸詩人的內(nèi)心真實封閉起來,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峽彼岸卻異軍突起。從“現(xiàn)代”、“藍星”、“創(chuàng)世紀”等詩社的興衰沉浮中,可以窺視臺灣現(xiàn)代詩歌對母語的回歸和探尋。這些詩人大都是從大陸抵達臺灣,其中紀弦、覃子豪、鐘鼎文等本來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現(xiàn)代派詩人。紀弦以筆名路易士活躍于詩壇,并與戴望舒創(chuàng)辦《新詩》月刊,1953年在臺灣創(chuàng)辦《現(xiàn)代詩》,繼續(xù)倡導和發(fā)展現(xiàn)代派詩。他提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西化”主張,瑏瑦對于輸入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流派的觀念和技巧,打破臺灣威權政治禁錮文藝的僵化局面,使詩人獲得創(chuàng)作自由,發(fā)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離了民族文化的傳統(tǒng),理當受到覃子豪等詩人的批評。在西方文化無遮攔地進入臺灣的特殊文化環(huán)境中,骨子里有著炎黃語言文化意識的臺灣詩人,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潮與中國古典詩歌、現(xiàn)代詩歌傳統(tǒng)的撞擊中站穩(wěn)腳跟,探尋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藝術軌跡。這就使?jié)h語詩歌的藝術轉(zhuǎn)變并未因為大陸的政治運動而中斷,新詩在海峽一隅獲得了生存環(huán)境和藝術發(fā)展。
在中國當代詩歌發(fā)展史上,臺灣詩歌不單填補了“”期間詩苑的空白,同時也最早進入與西方詩歌對話,在處于新詩發(fā)展的“前沿”充當了承上啟下的角色。倘若對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就會疏忽漢語詩歌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邏輯。臺灣五六十年代詩歌在變動的多元格局中呈現(xiàn)著生機,運用現(xiàn)代技巧進行自由的精神創(chuàng)造,已成為詩壇風尚。所謂“臺灣新詩長達近二十年的論戰(zhàn)”,表面上看是圍繞傳統(tǒng)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之間的沖突,實質(zhì)上“離心力”也受著傳統(tǒng)之力的制約。創(chuàng)世紀詩社以“新民族之詩型”為要旨,他們雖像游向大海的魚,因?qū)π庐惛械臒釕俣憩F(xiàn)了對傳統(tǒng)的遠離,但飄泊的游子最終心系本土的語言和詩歌藝術。從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這一過程的深刻體現(xiàn)。臺灣現(xiàn)代派詩歌的探索免不了帶有試驗性,但實現(xiàn)漢語詩歌轉(zhuǎn)變需要在充滿探險精神的試驗中實現(xiàn),關鍵在于這種試驗能否催促漢語詩歌藝術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種“無根”的試驗,必然帶來詩歌的“失血”,并因“飄泊無依”而生命孱弱。
臺灣詩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紀現(xiàn)代詩人的口語敘述的影響,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語化詩風,與戴望舒、卞之琳的現(xiàn)代詩風一脈相承。現(xiàn)代漢語自由體詩的口語化,是一個動態(tài)的詩學概念,不僅使詩性言說處于不斷變化的時代語境之中,同時還能注入和激活詩的現(xiàn)代漢語的質(zhì)素和精神,消解新詩創(chuàng)作中揮之不去的譯詩化印記或模仿痕跡。艾略特曾稱現(xiàn)代最佳的抒情詩都是戲劇性的。我們已有卞之琳把“戲劇性處境”、“戲擬”的方式運用于詩創(chuàng)作中的成功經(jīng)驗。曾專修過戲、演過戲的痖弦,擅于把“戲劇性”化為詩的因素,活用為一種睿智機巧的口語敘述方式。在痖弦的詩中,這種戲劇性表現(xiàn)又自然融匯于民謠寫實的詩風之中,形成了詩人的自然淳樸而又諧謔或嘲諷的現(xiàn)代口語抒情腔調(diào)。詩的“戲劇性”,旨在構成詩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詩人進入“乞丐”的體驗角色,充當敘述者,又是被敘述者。敘述口語,既具有濃厚的民謠腔調(diào),又是充滿戲劇性氛圍的詩性表現(xiàn)。于俗常的喜劇調(diào)侃中構成諷喻人生的無奈和悲劇的深刻意味。痖弦獨特的敘述口語方式,表面上通俗輕松,且?guī)в幸环N甜味,而骨子里卻是深沉的,包含著傳統(tǒng)的憂苦精神。
“新民族之詩型”揭示了漢語詩歌藝術的內(nèi)涵:“其一,藝術的,非理性之闡發(fā),亦非純情緒的直陳,而是意象之表現(xiàn)。主張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國風的,東方味的———運用中國文學之特異性,以表現(xiàn)出東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國自由體的口語化離不開新詩的漢語藝術傳統(tǒng),不可不發(fā)揮漢語“意象”、“意境”和“東方味”的優(yōu)勢。應該說,余光中、鄭愁予等詩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創(chuàng)世紀”詩人更明顯地表現(xiàn)了發(fā)揚漢語詩歌傳統(tǒng)的藝術自覺。早期作為現(xiàn)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詩風回歸傳統(tǒng);鄭愁予被公認為臺灣詩壇最富有傳統(tǒng)精神的現(xiàn)代詩人。他們致力于漢語詩歌的美麗意象和音韻流風的捕捉,把握漢語字詞組合和修辭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離別磨亮”(鄭愁予《水手刀》),“小時候/鄉(xiāng)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余光中《鄉(xiāng)愁》),像這種現(xiàn)代口語的抒情詩句,因意義的斂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藝術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視詩的音樂性的傳統(tǒng),將古典詩詞的聲韻音色的美融于現(xiàn)代口語的自然韻律之中。余光中批評某些現(xiàn)代詩讀起來“不是啞,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現(xiàn)象,認為“藝術之中并無自由,至少更確實地說,并無未經(jīng)鍛煉的自由。”瑏瑨現(xiàn)代詩人不是著眼于字面的抑揚頓挫,而是以文字來表現(xiàn)情緒的和諧,以現(xiàn)代人的感覺和情緒融入詩的音節(jié)和節(jié)奏,情緒的起伏跌宕構成詩的韻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獨創(chuàng)形式,構成了內(nèi)在情緒與口語音節(jié)的高度融一。
實現(xiàn)古典詩詞藝術向現(xiàn)代漢語詩歌轉(zhuǎn)化的難度在于向內(nèi)心的突入,對現(xiàn)代口語的詩性表現(xiàn)功能和審美趣味的開拓。洛夫在跟語言的搏斗中尋求“真我”口語意象。他在詩集《無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稱這輯詩最大的特征,“是盡可能放棄‘文學的語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語言’”。這既避免了詩的語句的“枯澀含混”、意象的“游離不定”,同時詩意也“不致僵死在固體的語義中”。當然,生活口語以實用的傳達為目的,詩的語言乃是表達,是一種審美形式。洛夫多年來從西方超現(xiàn)實主義的詩與中國悟性的禪的相通中尋求口語意象的內(nèi)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質(zhì)。超現(xiàn)實主義的“自動語言”與禪的“拈花微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超現(xiàn)實主義詩人認為,只有放棄對語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詩才能擺脫虛假浮出水面;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無法回歸人的自性。可見“自動語言”與“拈花微笑”都是企圖表現(xiàn)潛意識的真實。洛夫采用這種表現(xiàn)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動語言”反邏輯語法的傾向。他著眼于禪的悟性與超現(xiàn)實主義的心靈感通的契合點,發(fā)揮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無窮之意趣的審美效果。洛夫主張的“約制超現(xiàn)實主義”,更融入了現(xiàn)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種具有新的美學內(nèi)涵的現(xiàn)代漢語方式,這種語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類經(jīng)驗的本身,而且又不斷改變平常習慣語言的意義。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證。
盡管還不能說臺灣詩壇已經(jīng)產(chǎn)生成熟的現(xiàn)代漢語詩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臺灣現(xiàn)代詩尋求回歸和再造傳統(tǒng)的藝術經(jīng)驗,卻也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藝術建設的動人景觀。
四、新時期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的形成,對新詩體形式再度誤讀還是著力探尋?
新時期詩歌變革與世紀初詩體解放一樣,側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覺的詩歌藝術革命,然而也是背負著大半個世紀的新詩經(jīng)驗而進入新鮮廣闊的世界。中國古典與現(xiàn)代、西方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臺灣40年各種詩歌藝術和詩潮,紛至沓來,構成新時期詩歌豐富復雜、迷離激蕩的背景,這醞釀了一場根本性的藝術轉(zhuǎn)變———新詩由充當“工具”回歸精神家園。這不是簡單的回復,而是在詩的現(xiàn)代化意義上的抵達。世紀初詩體解放屬于語言形式本身的變化,是通過思想解放而達到詩體語言的解放(自由)。新時期詩歌語言由充當政治工具的角色,轉(zhuǎn)變?yōu)殪`魂和生命的存在(棲所),是作為載體、媒介的詩歌語言發(fā)生了根本性質(zhì)的變化,是通過思想解放回歸詩的本質(zhì)意義上的本體。具體表現(xiàn)為詩人由“代言人”向個人化寫作的轉(zhuǎn)型、由對社會、人生的詠嘆到生命體驗的突入,詩性言說由大一統(tǒng)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轉(zhuǎn)型、由傳統(tǒng)的抒情向抒情與敘述的分延。從而大大拓展了詩性表現(xiàn)的領域,形成現(xiàn)代漢語詩歌超越傳統(tǒng)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當一批老詩人以傳統(tǒng)的抒情方式唱著“歸來者”的歌,朦朧詩崛起,揭開了個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朧詩人開始因個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藝術手段帶給詩壇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的“我”與詩人個人的“我”之間的反差。而消除這種差距,意味著詩人找回丟失的自我,返回內(nèi)心體驗的真實。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現(xiàn)象,是在對“左”的政治和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現(xiàn)出的個性自由精神和嶄新的理想主義的光輝,顯示了新時期中國人的心靈的蘇醒,是對“五四”新詩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精神的張揚。在藝術上,與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相銜接。特別是戴望舒詩歌講究旋律和意象的朦朧美,穆旦詩歌的凝重和現(xiàn)代知性———充沛堅厚的主體精神,對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發(fā)生了積極的影響或心靈感應。詩人的群體意識與“代言人”,是有著明顯界限的不同概念。個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詩人切入社會和人生的群體意識傾向。如牛漢的《華南虎》、《夢游》,曾卓的《懸崖邊的樹》、《有贈》,邵燕祥的《五十弦》等,總是以強烈深厚的個人情感的詩性抒發(fā),表現(xiàn)了對社會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經(jīng)驗的凝聚力。“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一樣要遵循個人化的抒情。只是體驗的角度不同。新時期詩壇的“李瑛現(xiàn)象”,可以視為現(xiàn)實主義詩人的個人化抒情的藝術實現(xiàn)的反映。這位隨同共和國的步伐走過半個世紀的創(chuàng)作生涯的詩人,從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體發(fā)生了由戰(zhàn)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詩人個人化的劇變。李瑛詩歌創(chuàng)作從此走出了不少老詩人走不出的困惑。詩人自我意識的強化,并未改變對人民關懷的初衷,從李瑛詩歌的穿透時空的廣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帶有凝重的歷史感、滄桑感。當朦朧詩沉淪之際,卻是李瑛、老鄉(xiāng)、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現(xiàn)實主義詩歌興起之時,這說明個人化抒情已成為新的抒情傳統(tǒng)。它不會因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種語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陳敬容、杜運燮、鄭敏等現(xiàn)代詩人,當年就是以個人化抒情而步入詩壇,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而不衰。朦朧詩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和發(fā)展,朦朧詩人又不能調(diào)整自己,確立新的正面現(xiàn)實的勇氣和位置,勢必使詩喪失了原先的震驚效應。倒是舒婷抒寫愛情、楊煉吟詠歷史等詩篇,留下了較長的回音。朦朧詩的批判精神和個人化抒情的風格,不會過時。朦朧詩對新詩體雖然沒有多大突破和創(chuàng)造,但在意象營造中充滿才情和奇想的隱喻方式,具體清晰而整體朦朧的特征,仍是對新詩的漢語藝術特性的發(fā)揮和創(chuàng)新。我們不能認同朦朧詩“仍是以西方詩歌為原型的漢詩”的說法,瑏瑩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朦朧詩中有模仿西方詩歌的跡象,這在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中尚屬罕見。從朦朧詩中仍有名句傳世這一事實,也能說明這些篇什已經(jīng)具備現(xiàn)代漢語詩體形式的某種特征。朦朧詩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將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傳統(tǒng)繼往開來。他們遠離“社會中心”,避開塵囂,為世紀的落日鑄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構心靈———語言的棲所,展示承受人類苦難的靈魂。
詩如何表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人的真實存在,表現(xiàn)生存體驗的原生態(tài)?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詩學命題。在后新詩潮興起與海峽兩岸發(fā)生詩藝交流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口語化敘述的詩風。這種客觀陳述的詩性言說,直接進入生命存在,表現(xiàn)生命的脈息,敲擊存在的真髓,更能顯現(xiàn)詩歌語言的真實和本色,消解了傳統(tǒng)抒情中容易出現(xiàn)的浮夸和矯飾。后新詩潮對詩風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適應這一新的表現(xiàn)領域的客觀陳述的轉(zhuǎn)型,起了啟動和推動作用,而在敘述方式上則帶有隨意性、翻譯性語感化的傾向,消減了詩的形式價值。特別是有些青年詩人的才華浪費在對“不可知的生命內(nèi)部”的探索。當后新詩潮匆忙演繹西方詩的“后現(xiàn)代”時,臺灣那脈口語化敘述的詩風,由于歷經(jīng)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尋民族語言本性的過程,則以初步入乎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語言姿勢,影響了大陸詩歌的語言轉(zhuǎn)型。林染、馮杰等一批中青年詩人對臺島詩風很快產(chǎn)生感應,潛心于自身生存環(huán)境的體驗,凸現(xiàn)詩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審美特征和本土氣息。90年代新潮詩人也開始自我調(diào)整,正面現(xiàn)實人生和社會歷史。如同屬對女人的愛情體驗,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與被稱為“黑洞意識”的《女人》組詩明顯不同,詩人從社會現(xiàn)實的大環(huán)境中探測“黑洞”,表現(xiàn)了對母女兩代人的愛情悲劇的痛苦體驗的深度。一種詩風并不單單因為起于新潮而盛行,還在于它是否擁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擁有母語的力量。
一種新的詩風的流行,可能意味詩的新變和發(fā)展,但并不表明詩的成熟。90年代詩歌因趕“風”、隨“風”而導致大面積“仿制”、“復制”的現(xiàn)象,乃至使敘述口語變?yōu)樵娙巳锏摹靶性挕?造成詩歌語言的飄浮或套式。所謂“口語”也成了讀者難懂的“咒語”。新詩的語言形式,成了20世紀尚未很好解決的遺留問題。
不管是口語化敘述還是個人化抒情,都只是作為一種詩性言說的方式,具有傳達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本質(zhì)意味的可能,但建構相應的語言形式,卻是需要反復琢磨、獨具匠心的智性創(chuàng)造的藝術過程。新生代詩人以“現(xiàn)代漢詩”自詡,但又很少有人重視對現(xiàn)代漢語詩體的探尋。他們以“的《嘗試集》也是從一種語言方式向另一種語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證瑐瑠,以在“一張白紙”上標新立異為榮,認同世紀初把自由體誤讀為“無拘無束”、“散漫無紀”。這似乎成了中國詩歌變革的劣根性表現(xiàn)。至于還抱著“左”的新詩傳統(tǒng),“九斤老太式”地數(shù)落新時期詩歌的論者,卻也不講詩的語言形式,在他們看來完全是“內(nèi)容決定形式”。只有那種飽經(jīng)詩壇必要憂患而又長于藝術涅*$的詩人,終究悟出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真正含義;只有那種操守純正的詩歌藝術、走著自己寂寞的路的詩人,懂得要寫什么樣的詩。真正優(yōu)秀的詩篇,總是離不開漢語藝術的獨到、精當、奇妙和高超的表現(xiàn)力而動人傳世。
正如世紀初詩體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詩建設,新時期詩歌的本質(zhì)意義的回歸,必然也伴隨對詩的語言形式的探尋。新詩的現(xiàn)代漢語言藝術的成熟,必將由新世紀詩人去收獲。
注釋:
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頁。
②參見《談新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294—311頁。。
③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
④劉半農(nóng)《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3卷3號。⑤郭沫若《鳳凰·序我的詩》,重慶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萊的詩·小序》《創(chuàng)造季刊》1卷4期。
⑦郁達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時事新報·學燈》。
⑧《創(chuàng)造月刊》1卷1期。⑨《語絲》第82期,收入周作人《談龍集》,北新書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發(fā)《食客與兇年·自跋》,北新書局1927年5月版。
11。聞一多《詩的格律》,《晨報副刊·詩鐫》7號。瑏瑢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語,上海復興書局1932年版。
14。艾青《詩論》(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